Dec 17, 2025
作者:李维
时间是记忆最大的敌人。香港2019年的社会运动,转眼已过去六年,许多当时一手的媒体直播早已散失,多家独立媒体近年来都迫于政治压力而关闭,社交媒体上两极分化的碎片化叙事,更是有意无意地重构了公众的认知。
六年前的11月中旬,香港多所高校的校园成为战场,警民冲突在香港理工大学内部及周边尤为激烈,警方包围校园近两周,大量示威者被捕。如今,理大冲突的火光已熄,无论是亲历者还是旁观者,还有多少人清晰地记忆着当时的场景?
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的大陆人,我感受到了这种认知的断裂之深:许多认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朋友,依然难以理解当时“勇武派”抗争者为何要选择激进的“以武制暴”。即便查阅第三方资料,如维基百科的“香港理工大学冲突”、“香港中文大学冲突”、“香港黎明行动”、“破晓行动”、“晨曦行动”、“曙光行动”等词条,我们读到的也多是关于暴力冲突的描述。这种困惑在面对2019年11月香港高校校园内的火光时,往往会变成一种本能的排斥与不屑。
正是在这样记忆的迷雾中,纪录片《理大围城》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这部影片不加渲染,拒绝宏大叙事,记录了运动中的个体和细节,将观众带回香港理工大学的红墙内,一同经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要看懂《理大围城》中年轻抗争者的处境,必须先理解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的宏观背景。
 2019年10月1日,香港街头游行场面。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2019年10月1日,香港街头游行场面。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这场运动始于2019年6月,最初是为了反对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该条例允许将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尽管有上百万人参与和平游行,政府初期的强硬态度和警方的武力驱散,导致部分示威者认为和平手段已无法奏效。
于是,运动中逐渐分化出一支被称为“勇武派”的力量,他们主张用更为激进的手段,包括破坏公共设施和与警方正面对抗,来迫使政府回应民间提出的“五大诉求”,其中包括撤回修例和落实真普选。到了2019年下半年,向来推崇“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香港民主派与“勇武派”形成了独特的互助关系,被称为“和勇不分”,即和平示威者在道义和后勤上支持前线“勇武”抗争者,而“勇武”抗争者则试图通过“以武制暴”来确保运动不因警暴而收场。
2019年11月的校园冲突,正是这种对抗升级的顶点。当月发生的港科大学生周梓乐坠落身亡事件,成为局势恶化的直接导火索。“勇武派”以此为由,号召在11月11日发动“黎明行动”,意图在天亮前通过瘫痪交通来强制实现全港“三罢”——罢工、罢课、罢市。
抗议者选择占领大学校园,基于战略考量:香港中文大学毗邻连接新界与深圳的交通大动脉——吐露港公路和东铁线;而香港理工大学则紧邻连接九龙与港岛的核心通道之一——红磡海底隧道。抗议者试图通过控制校园,向这些交通干道投掷杂物,从而威胁香港的经济命脉以向政府施压。
面对抗争者的行动,香港警方打破了常规。大学校园在法律和传统上通常被视为警方的禁区,除非接获报案或取得搜查令,否则警方不得擅自进入。然而,抗争者对校园的占领和对交通的阻塞成为了警方强力介入的理由。
11月12日晚,中大“二号桥”发生了标志性的激烈冲突,警方发射了逾2000发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抗议者则主要以汽油弹回击。当警察在夜间撤离后,一些抗议者误判这是一场战术胜利,随即信心满满地转战香港理工大学。不料,香港警方将理大校园包围,校园内的抗争者进退两难,直到11月28日警方才解除封锁。
 2019年11月12日晚间,抗议者与警方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发生激烈冲突。图片来源:众新闻
2019年11月12日晚间,抗议者与警方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发生激烈冲突。图片来源:众新闻 2019年11月13日,抗议者控制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图片来源:Studio Incendo
2019年11月13日,抗议者控制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图片来源:Studio Incendo《理大围城》没有试图铺陈上述复杂的历史背景,而是将叙事焦点精确地锁定在危机最尖锐的时刻:从2019年11月17日警方彻底包围校园,将抗议者困成“瓮中之鳖”,到次日晚多名中学校长进入校园试图带离学生的最初两天。
影片由“香港纪录片工作者”匿名制作,绝大部分镜头中抗议者的面部被打上马赛克(为了确保被捕人士不被警方“消失”,有抗议者被捕的镜头中,被捕者的面部在影片中清晰显现),这种去个人化的处理反而强调了这是一种群体的共同命运。影片不进行道德审判,不提供全知视角,只是带领观众进入那个封闭、压抑且充满恐惧与绝望的红砖围墙之内。
包围之初,年轻的抗争者们颇有兴致,与校外的警察喊话,还用扩音器放着辱骂警察的说唱。而警察也用喇叭向校内的抗争者劝降,还放出《十面埋伏》等歌曲。但这和香港2019年的其他警民冲突一样,根本不是一场对等的冲突。警察有着充足的支援,拿着高额的加班费,有着装甲车、水炮车、“声炮”、催泪弹、橡皮子弹以及真枪实弹。而抗争者的攻击性武器主要是汽油弹(在《理大围城》中也出现了弓箭),而其它装备主要是防卫性的雨伞和放毒面罩。
很快,抗争者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冲出重围意味着直接遭到逮捕和暴力对待;尝试跳下天桥或钻下水道逃生则面临伤亡的风险;选择投降登记则意味着日后法律的追责和长期的牢狱之灾;而留守校园则要忍受精神崩溃和弹尽粮绝的折磨,寄希望于渺茫的“围魏救赵”,即校园外的抗争者试图从外围冲破警察的封锁。
到了理大围城的第二晚,有许多中学的校长被警方允许进入校园,带领抗议的学生走出校园。警方允许抗议者当晚回家,但必须与警方登记。虽然有抗议者反对校长的介入,但是许多学生默默地选择和校长们离开。
最令人难忘的场景,要属影片最后两个少年在台阶上犹豫不决的样子。他们看着下方已经撤离“投降”的学生,又时不时地回头看留守的战友,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出什么选择。个体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也是所有香港人在2019年需要做出的抉择。
《理大围城》没有解答——也没有试图解答——许多人对“勇武”的疑惑:为什么“勇武派”造成破坏,民主派却选择“和勇不分”?为什么“勇武派”失策被围攻,但许多香港民众依然同情年轻的抗争者,而压倒性的民意,使民主派在2019年11月24日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横扫全港十八区的大多数席位?
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香港2019年社会运动的历史意义,恐怕需要更长的历史维度才能显现。制作《理大围城》的“香港纪录片工作者”记录了可能被噤声的视角,抢救了容易被忘却的记忆,为帮助后人理解香港的历史尽到了一份责任。
与《理大围城》相对的,是中国官方针对香港民主运动的一系列话术与叙事。早在2016年,新华社发布新闻报道禁用词中就特别加入了对于香港抗争运动的“规范”称呼:
对港澳反对派自我褒扬的用语和提法要谨慎引用。如不使用“雨伞运动”的说法,应称为“非法‘占中’”或“违法‘占中’”;不称“占中三子”,应称为“非法‘占中’发起人”,开展舆论斗争时可视情称为“占中三丑”;不称天主教香港教区退休主教陈日君等为“荣休主教”,应称为“前主教”。
而2019年,反修例运动在一开始就被官方定性为“暴动”,致使运动过程中的五大诉求之一就是要求港府撤回“暴动”认定。对于反修例运动中的参与群体,中国新闻中的常用指代语包括“暴徒”、“恐怖分子”、“乱港分子”。
因为中国大陆的信息封锁和无孔不入的新闻审查,不难想象,大部分中国公众对这场运动的认知跟上述官方叙事出入不会很大。而在当下,因为2020年国安法的实行,中央对香港言论的全面镇压,在香港曾经存在过的与官方话语相异的叙事和记录,已经很难进入中文公众视野。
可见,官方深谙孔子“必也正名乎”的统治理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权力自史以来就对语言充满警惕,因为独立的叙事具有对正统的破坏力量。
随着官方的“禁用词”和定性,针对香港社会运动的记忆改造工程早已开启。如果持续下去,多年后的大陆和香港公众,也会逐渐因此而丧失对整场运动的理解的可能性,可能进而演化为漠不关心。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需要看到2019年在运动现场、在事件发生的中心,“香港纪录片工作者”在《理大围城》等纪录片中记录下不同个体、侧面、瞬间的价值。这些记录并不是试图定义整场运动的正义性、历史意义和结论,但会保存下被官方话语覆盖、屏蔽、湮没的事实、让独立的记忆成为真正的可能。
本期推荐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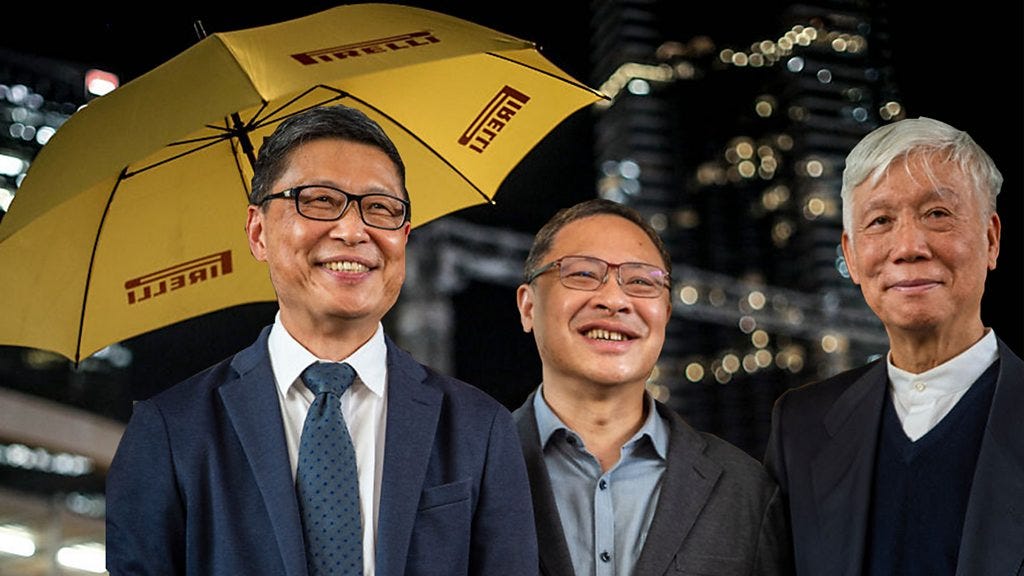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