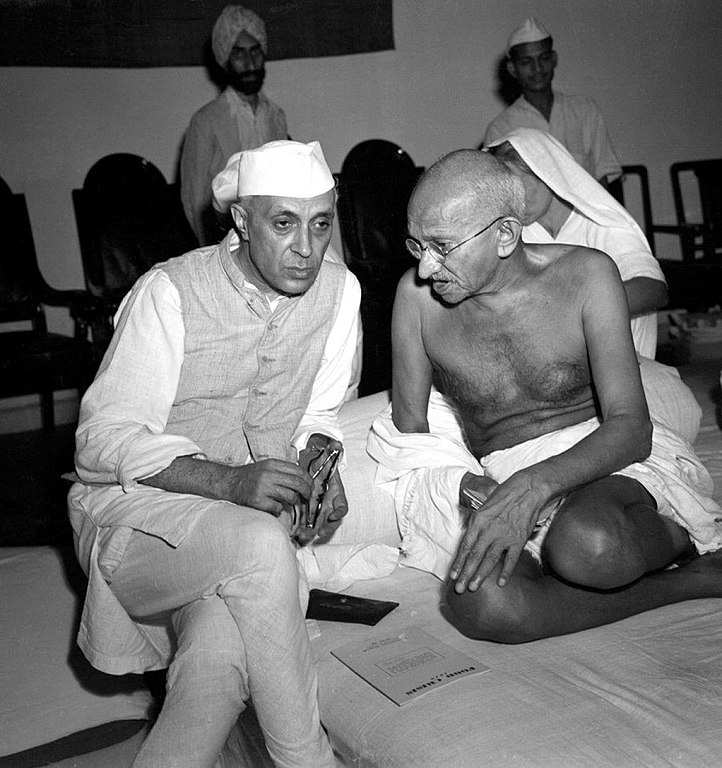第十四章 「走!走!今夜就走!」
(一)
一夜平安。
宿鳥飛出窩巢,站在樹枝上,抖抖翅膀,發出清脆的啼鳴。夜色漸漸褪去,天終於亮了。這天是1959年3月17日,藏曆土豬年2月初8日。
羅布林卡花園開始蘇醒。御馬廄裡的馬打著響鼻,馬夫飼養的猴子拴在馬廄前的木柱上,拖著長長的鏈子上竄下跳。池塘邊的野鴨伸長脖子嘎嘎叫著,接二連三跳進水裡,受驚的魚一甩尾巴,忽一下潛到深處。
達旦明久頗章裡,電燈早早就亮了。達賴喇嘛照常在日出前起床,御膳房送來準備好的酥油茶和早餐。達賴喇嘛喝過茶,到經堂去念經打坐。侍從們輕手輕腳地走動,輕聲輕氣地說話,唯恐驚擾他。
太陽升起後,夏宮裡開始正常的活動。門口值夜班的警衛們換崗,侍從們來來往往,給噶倫和經師們送茶送飯,園丁提著水桶,為宮殿門前的花木澆水;在牆外安營紮寨的人們打著哈欠鑽出帳篷,有的圍著羅布林卡轉經,有的對著宮殿磕長頭。有人撿來枯枝點火煮茶,一道道青煙裊裊上升,融合在清晨的霧靄中。
路上開始有行人來往。林仁波切的僕人赤列朋措做完例行的雜事,走出仁波切的莊園,丹巴索巴也離開了住處。二人住在拉薩不同的地方,那天清早不約而同,都朝羅布林卡走去。這時候,一些民眾代表離開羅布林卡,去德吉林卡的印度領事館,借用那裡的發報機給當時在噶倫堡的夏格巴發電報,通知他說西藏已經獨立,請他通知印度政府和聯合國,派人來調查。
上午,達賴喇嘛召集噶倫們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金色頗章開會,討論如何避免戰爭。「拉薩事件」已經爆發一個星期了,羅布林卡四周還有幾千民眾,一旦解放軍動武,勢必血流成河。前一天阿沛‧阿旺晉美派人送來幾封信,其中有一封是寫給噶廈的,這封信噶廈尚未答覆。西藏政教的最高層討論了半天,覺得唯一的辦法是給譚冠三去信,請求他不要動用武力驅散人群,讓噶廈再次努力說服民眾撤離。他們給阿沛回信說,民眾頭腦簡單,被情緒控制,但仍有可能撤離,噶廈會繼續努力。目前民眾事實上控制了羅布林卡,達賴喇嘛去軍區很困難,形勢好轉後,他一定會去。他們還附帶了一份密碼,說再次來信最好使用密碼。
把信送出羅布林卡頗費了一番周折。大門口的民眾志願警衛對官員們極不信任,所有外出的人都被盤問搜查,特別是從宮裡帶出去的信件。這封信如果被民眾看到,一定會引起極大恐慌。噶倫們想了各種辦法,最後,噶倫柳霞派一名僕人假裝買東西,把信帶出去,交給了阿沛。
3月10日以來,羅布林卡和工委之間已經無法直接聯繫,噶倫阿沛‧阿旺晉美成為兩方唯一的聯繫管道。至今沒有資料顯示,阿沛當時是否了解中方的意圖和中方的軍事部署。1989年3月出版的《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中,收錄了原噶廈政府秘書格杰巴‧丹增多吉的一篇回憶文章。根據他的回憶,3月14日,他曾受索康等三位噶倫的派遣去見阿沛,帶去口訊:
因前天勝寶向人民代表頒發了指令,不准召開會議,將他們趕出了羅布林卡,同時還在想一切辦法穩定局勢。漢人方面有何動向,請指示。」另外還呈送了一本密碼簿,並說:「以後向噶廈寫信時請用此密碼撰寫。」我按此旨意,詳細地向阿沛作了匯報。阿沛聽完後說:「這次不是完了嘛,如諸地王決心這樣幹的話就是這種下場。難道漢人方面不作充分的準備嗎?因我家住在拉薩大橋附近,能聽到汽車晝夜不斷地來來往往的聲音。
從他的回憶來看,阿沛認為噶廈參與了「拉薩事件」,但達賴喇嘛並沒有與他們「合謀」。而且,3月14日,軍委已經給入藏部隊發出了預先號令,阿沛顯然不知情,他只是根據拉薩大橋上軍車晝夜來往這一現象,判斷軍區在作軍事部署。
阿沛匆匆寫了張條子,表示信收到了,認為達賴喇嘛去軍區的計畫很好,還說將會寫封更詳細的信。
紙條帶回羅布林卡。達賴喇嘛和噶倫們再次來到金色頗章開會,討論如何回覆。這時候,已經是拉薩時間下午一點多,也就是北京時間下午三點多。
會議正在進行,羅布林卡北面突然傳來巨大的爆炸聲。此時丹巴索巴正在北門邊,看到一發砲彈呼嘯而來,落在離羅布林卡約200多米的濕地裡,泥水飛濺。人們還沒明白出了什麼事,又一聲爆炸。
夏宮內外靜默片刻,緊接著傳來驚惶的呼喊:「砲彈!」「漢人開砲了!」「漢人要進攻了!」「要打仗了!」
黃牆圍繞的內宮裡,腳步聲、呼喊聲、拉槍栓聲響成一片,警衛們有的衝向大門口,有的衝向達旦明久頗章。一名噶倫衝出金色頗章,跑到大門口,高聲喊叫,叫志願警衛隊不要還擊。
會議室一片死寂,空氣彷彿凝結。所有的人同時想道:「開始了!」
局勢顯然已經不可逆轉。
大家不約而同轉過頭,望著他們的領袖,會議室裡最年輕的僧人。雖然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但決定還是只能由他來做。
是走?是留?這是一個關係到西藏前途和命運的決定。這位未滿24歲的青年僧侶臉色蒼白,一手扶頭,沉默不語。
半晌,他輕輕吐出一個字:“Kuten”。
(二)
西藏國家神諭,第十三任乃穹神諭洛桑晉美帶著幾名助手,匆匆來到經堂,走進佛像旁邊的小房間。
藏語Kuten,意為「神諭」,即「降神者」。在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中,神諭有重要作用。Kuten這個詞的本意是「基礎」,也就是說,神諭只是護法神的「身體基礎」,他的作用是讓護法神通過他的身體降臨,回答達賴喇嘛或者噶廈政府提出的問題。藏區有許多神諭,其中最重要的是乃穹國家神諭。他所降之神,是護法神多杰札登。
乃穹神諭有悠久的歷史。傳說蓮花生大師入藏的路上,一路「有力鬼神多有前來試道」,面對前來挑戰的鬼神,大師「以身、語、意三密無邊法力,收其命根,使其發誓聽命」。建立桑耶寺之前,「蓮花生大師降伏所有八部鬼神,令其立誓聽命,建立鬼神所喜之共祀,歌唱鎮伏鬼神之道歌,在虛空中作金剛部舞,並加持大地地基等」。
「八部鬼神」,即苯教信奉的瘟神、山神、地神、本土神、游神、龍神、獨腳鬼,和作祟鬼。傳說蓮花生大師運用超凡的能力,調伏了十二丹瑪女神,雪山長壽女神,降伏念青唐古喇山神等許多神靈,在「令其立誓聽命」後,根據他們的法力,將這些神靈指派為佛教的護法神。最後,只剩下五個法力高強、桀驁不遜的神靈拒絕聽命。蓮花生大師與這五個神靈進行了一連串惡戰,最終降伏了他們。
五神靈之一化為八歲小童,代表另外四個來見蓮花生大師,表示歸降,並願效忠。蓮花生大師拿起一枝象徵霹靂的金剛杵,在小童頭頂打下一個印記,在他的舌尖上塗了一點花蜜,然後封他為佩阿嘉頗(Pehar Gyalpo),令他們成為佛教護法神。由於佩阿嘉頗過於威猛,不能直接與世間接觸,必須通過一些聖器作為「物質基礎」,才能與他們溝通。蓮花生大師將這些聖器安置在桑耶寺。即便如此,佩阿嘉頗也不能與人類相通,降神時,前來的只是他的主要助手多杰札登。這個傳說只是有關多杰札登的眾多傳說之一。民間還流傳著其他不同的傳說。
佩阿嘉頗成為西藏政府的守護神,始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他親自督建拉薩城外的乃穹寺,並且把佩阿嘉頗的聖物從桑耶寺遷至該寺供奉。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位期間,乃穹寺僧人從第五世達賴喇嘛指定的101人增加到115人。由於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與護法神佩阿嘉頗的特殊關係,每當需要作出重大決策時,達賴喇嘛或者噶廈政府就會通過乃穹神諭來尋求護法神的指點。
過了一陣,洛桑晉美穿著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蹌蹌走出供他降神後休息的小房間。他身穿色彩斑斕的錦緞法衣,足蹬藏靴,胸前綴一面亮閃閃的圓型護心鏡,背後斜插四枝三角旗,頭戴裝飾羽毛、骷髏和鈴鐺的高冠。這套法衣從裡到外足足有八層,頭上的高冠重達30磅,全身裝束重達70磅。這套裝束使神諭舉步維艱,只能在助手的攙扶下蹣跚而行。
鼓號響起,僧侶開始誦經。在眾人緊張的注視下,洛桑晉美漸漸進入迷狂狀態。他甩開助手,踉蹌幾步,隨即拔出寶劍,用尊貴的步伐緩緩起舞。他的身體開始膨脹,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彷彿全然消失。陡然間,他發出一聲高喊。那聲高喊不僅改變了在場所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西藏的歷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線圖。助手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解開繩結,取下碩大的高冠,護法神脫體而去,洛桑晉美頹然倒地。
這時,已經是3月17日下午,北京時間4點多。
這天,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西藏局勢。與會者的意見是:「最好設法讓達賴留在拉薩,他若硬是出走,這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因為我們現在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政府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
(三)
在作出重大而困難的決策前請示神諭,是藏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請示神諭體現了藏人對世界和自身關係的理解。從人類學和宗教學的角度來看,神諭這一文化現象,是理解藏文明的一把鑰匙,也是理解西藏社會和歷史的必由途徑。因此,近百年來,曾經到過西藏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宗教學家,都對藏民族請示神諭的做法,抱持探索、理解和尊重的態度。可惜,對於1959年來到拉薩的中國軍人來說,這些文化現象只能凸顯他們自己的「先進性」,藏人視為神聖的神諭,是他們嘲笑的對象。
半個多世紀後,在達蘭薩拉法王府採訪時,我問達賴喇嘛:「當您做重大決策時,為什麼總會請乃穹神諭降神?您覺得他的預言可靠嗎?」
「我今年70多歲了,請教乃穹神諭差不多有60年,」達賴喇嘛說,「我不記得乃穹說錯過,一次都沒有。」
「那麼,」我接著問,「您覺得乃穹對您的決策有決定性影響嗎?」
「不完全如此,」達賴喇嘛回答,「乃穹神諭的話只是供我考慮的因素之一。我還會參考其他因素。」
1959年3月17日那天,「其他因素」無疑就是那兩發砲彈。達賴喇嘛的兩部自傳中都提到,那兩發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是促使他做出決定的主要原因。參與決策的藏人在回憶錄中,也都提到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對他們產生的震動,以及對達賴喇嘛出走的影響。1959年4月18日,達賴喇嘛一行到達印度後,向國際媒體發表了第一份聲明,其中提到「兩三發射向羅布林卡宮的砲彈」,使大家意識到達賴喇嘛面臨極大危險,因而決定出走。
達賴喇嘛發表上述聲明兩天後,中國政府以「新華社政治記者」的名義,對國際社會公開發表〈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斷然否定「兩發砲彈」一事:
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三月十七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三月十七日,迫擊砲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砲」,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砲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裡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麼偏偏只打兩三發砲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既然否定了朝羅布林卡打過兩砲,自然沒有必要提及開砲的原因。很多年來,3月17日中方是否朝羅布林卡發射過兩發砲彈,一直是個未解之謎。
直到30多年後,「兩發砲彈」之謎才被無意中破解。1993年10月出版的《西藏平叛紀實》中,作者吉柚權首次披露,「兩發砲彈」確有其事:
(17日早上)叛亂武裝……連續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進行挑釁性射擊,密集的槍彈打壞了該站許多門窗,氣焰非常囂張。該站的經濟警察曾惠山對叛亂武裝的這種挑釁非常氣憤,沒有請示任何人就用60迫擊砲還擊了兩發砲彈,砲彈落在羅布林卡北面圍牆以北兩百至三百米處爆炸……
作者雖然透露一個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羅布林卡開了兩砲,但是沒有說明運輸站這樣一個非軍事單位為什麼擁有60迫擊砲,也沒有說明何以「經濟警察」可以操作砲。
1995年出版的《西藏黨史大事記》延續了《西藏平叛紀實》的說法,承認一個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羅布林卡開了兩砲:
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十六日突然向青藏公路拉薩運輸站連續開槍射擊。運輸站處於羅布林卡、藥王山、布達拉宮等叛亂武裝據點的半圓形包圍中,是叛亂集團之間的一個咽喉。十七日,聚集在羅布林卡北側的叛亂武裝又向運輸站射擊,並向運輸站的油庫、碉堡發射砲彈三十餘發。該站經濟員警曾惠山擅自以60砲向敵還擊砲彈兩發,落在羅布林卡北圍牆以北的二百至三百米處。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黨史大事記》中記錄的這一事件日期有所改變,「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對運輸站的「挑釁」從「17日早上」變成16、17連續兩天。更重要的是,「叛亂武裝」不僅朝運輸站射擊,竟然還發射了30餘發砲彈。根據這一記述,3月17日當天,「叛匪」不僅打了第一槍,甚至還主動出擊,發動了一場相當規模的砲戰,而一直等待對方先動手的解放軍居然沒有反擊。這段紀錄中沒有提到砲彈是否爆炸。
1995年內部出版的《平息西藏叛亂》中,對「兩發砲彈」的說法與《西藏黨史大事記》基本相同,雖然沒有提到發射砲彈者的名字,不過指出他不僅是警察,還是民兵。也就是說,面對羅布林卡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其實是一個半軍事機構。
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對這件事的描述又加入了新的內容:
17日……叛亂武裝增加了挑釁活動,不斷向解放軍駐地、地方企事業單位進行射擊。其中,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遭到射擊的子彈最密集,拉薩油庫挨了30多發砲彈,油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下午3時許,運輸站民兵、經濟警察曾惠山違反軍區規定,擅自用60迫擊砲向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還擊了兩砲。砲彈落在羅布林卡以北圍牆外二三百米處。
照上面的說法,3月17日「叛亂武裝」已經開始向拉薩市的各解放軍駐地發動了全面進攻。如果確有其事,那麼1959年4月的新華社評論為什麼對此隻字未提呢?那時是最需要向國際輿論說明「平叛」理由的時候,竟然隻字不提連續兩天30多發砲彈攻擊拉薩油庫這樣嚴重的事情,無論如何是難以解釋的。
和所有此類衝突一樣,誰先開槍開砲,誰打了第一槍,直接影響輿論對各方行為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評判。1959年4月,是世界輿論對中國軍隊在拉薩「平叛」的正當性質疑最強烈的時候,如果「叛亂武裝」確已在3月17日就先發動了進攻,新華社評論必然會提出來以證明平叛之正當性。1959年4月不提,到2008年突然出現,那就只能證明,時至2008年,宣傳中仍然需要設法對五十年前「平叛」的正當性尋找理由,作出辯解。
在形勢極其緊張,上至中央軍委,下至軍區司令部都在加緊調兵遣將的時候,居然有民兵「違反軍區規定」擅自朝羅布林卡開砲,這本身就是個嚴重事件,恐怕沒有任何一支軍隊的指揮官能夠容忍這樣的事情。事後違令者即使不受軍法處置,至少也會對事件本身進行徹查。然而,從上述不同時期的描述來看,這一事件如果不是沒有調查清楚,就是只公布了部分訊息。
另一方面,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境外出版的藏方資料中,均未提到17日上午,藏人曾對運輸站進行過密集的「挑釁性射擊」,或者開過砲。當時達賴喇嘛還在羅布林卡,藏人這樣做無異惹火燒身,給達賴喇嘛帶來極大危險,因此很難想像藏人會主動向解放軍駐地和各單位射擊。然而,如果沒有某種原因,曾惠山突然朝羅布林卡發射砲彈,似乎也說不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許只能等到更多的資料面世,才有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釋。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兩發砲彈客觀上打破了雙方對峙的僵局,形勢急轉直下,促使達賴喇嘛作出決定。他相信,如果民眾不再有保護的目標,他們很快會離開羅布林卡,自行解散。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避免大規模流血。
(四)
在人類歷史這部大書裡,有無數強鄰入侵,小國覆滅,國君帶領臣屬倉皇逃走的故事。這些故事充滿野心、陰謀、霸道、無奈、惶恐、驚險、蒼涼,因此,「逃亡的國君」成為文學、戲劇和電影的常見主題。1959年達賴喇嘛的逃亡,不過是無數類似故事中的一個。但是,當這種中世紀常見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而且是在冷戰高潮的世紀中葉,故事的地點一邊是神秘的西藏高原,另一邊是同樣神秘的中國大陸;其主角一個是老辣的紅色帝王,另一個是年輕的雪域「神王」,這個故事就有了不同的意義。
表面上,整個事件隱含著「紅色中國」與「白色雪域」,「共產主義」與「宗教信仰」,昔日宮殿「中南海」與當日宮殿「羅布林卡」之間的秘密較量,但這較量的背後又隱含了「專制」與「自由」、「民族霸權」與「民族自決」等現代主題,其過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極大地刺激了世界各地人們的想像力。
因此,幾十年來,達賴喇嘛出走這件事,在國內外演化成許多不同版本。這些版本有的是小說,有的是演義,有的是宣傳,有的是想像,當然也不乏神秘化和戲劇化的解說,使達賴喇嘛出走這件事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首先,出走人數到底有多少?國外的敘述中通常避免提及具體人數,其原因在於,當晚離開羅布林卡的準確人數至今還是個謎。由於時間非常倉促,出走的安排雖然由帕拉統籌,但具體細節其實是由不同的人負責,因此,就連當事人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說明3月17日夜晚,包括侍從和警衛在內,到底有多少人離開羅布林卡,研究者只能根據各種資料研判出大致的數字。
中國出版的書中,往往給出各種來源不明的數字。《西藏平叛紀實》中,作者提到跟隨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的人數有600多人:
……叛亂武裝以解放軍開砲射擊為藉口,又以保護達賴安全為理由,當晚深夜挾持達賴從拉薩河南渡口逃向山南方向,叛亂武裝的上層集團六百餘人隨行。
《平息西藏叛亂》中有一篇題為「西藏平叛綜述」的長文,談到達賴喇嘛出逃時,也用了「600餘人」這個數字。
當時拉薩河然馬崗渡口,即中方文獻中所說的「老渡口」或「南渡口」,只有一條最多可載30人左右,形同一隻長方形大木箱的木船,3、4條牛皮船,每條最多可載10人,這還不算帶去的若干匹馬。渡船往返一趟至少30分鐘。以每小時渡過70人計,600多人渡河恐怕要費一整夜的時間15。而且,600多人離開羅布林卡,哪怕是分批離開,也很難不驚動牆外民眾,或者引起中方軍隊的注意。
也許是注意到了「600餘人」這個數字不合理,在《西藏解放史》中,出走人員的數字大幅減少,從600餘人減少到150人,並且提供了上述資料中沒有的細節:
15日,……上層反動分子加緊籌劃劫持達賴出逃的工作:擬定了一個150人的隨行人員名單;物色了7名年齡、相貌同達賴相似的僧人作替身,準備了與達賴喇嘛相同的衣服;選定了出逃的路線等。
3月15日當天,在拉薩找到7名與達賴喇嘛年齡相似的僧人並不難,但無論何時何地,要同時找出7名與達賴喇嘛年齡、相貌都相似的人,恐怕並非易事。該書沒有提供「替身說」的資料來源,實際策劃者帕拉和庫松代本的回憶錄均未提及「7名替身」這一細節。「7名替身」之說或許有好的戲劇效果,但這種無法考證的資料很難認定為史實。
該書沒有說明150這個數字是否包括僕從和警衛。離開羅布林卡時的警衛士兵是臨時安排的,並沒有在3月15日擬定。而達賴喇嘛本人的傳記和藏人的回憶中都說,跟隨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的只有80餘人,其中有些是途中加入逃亡隊伍的。
1997年,當年在塞班島訓練阿塔和洛澤等人的CIA教員羅杰‧麥卡錫出版了一本書,其中提到達賴喇嘛出走時曾安排了兩支偽裝隊伍,用來迷惑追擊者。他注明該資料來源於貢保扎西和阿塔訪談。可是,他們兩人都沒有參與達賴喇嘛出走的策劃,貢保扎西見到達賴喇嘛是他自己逃到印度之後;阿塔則是在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將近一周後才趕上逃亡隊伍,而且兩人自己的回憶錄中均未提及此事。很有可能,所謂兩支偽裝隊伍,只是帕拉安排在達賴喇嘛隊伍前後負責掩護任務的,羅杰‧麥卡錫誤解了掩護隊伍的目的。
根據藏方參與者的回憶,兩發砲彈爆炸後,民眾代表馬上來找噶廈。他們認為砲彈顯示中共軍隊在測試大砲,很可能過一兩天解放軍就會進攻羅布林卡。他們強烈要求噶廈安排達賴喇嘛去其他國家避難。
乃穹神諭降神後,走與留已經不是問題,怎樣走、去哪裡才是問題。
噶廈、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卓尼欽莫帕拉、庫松代本朋措扎西等人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噶廈傳達民眾代表提出的要求,並討論了出走的人員、時間和路線。計畫能否成功,關鍵的一點是不能驚動駐守在羅布林卡外面的民眾。一旦驚動民眾,立刻會有大批人自願護送達賴喇嘛,勢必引起解放軍的注意,如果軍隊出來攔截或者追擊,無疑會是一場惡戰,根本違背了出走的初衷。
為此,會議決定,事不宜遲,必須當晚離開,隨行人員除了達賴喇嘛的家人之外,3月10日之後一直在羅布林卡的三噶倫、兩位經師、帕拉、庫松代本、基巧堪布噶章,以及少數政府上層人士同時離開。為了不引起注意,這些人將分成三批過河,每批之間相隔約一小時左右。
從羅布林卡去山南有兩條路,一條從羅布林卡南面的然馬崗渡口渡過拉薩河;另一條路從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到曲水或貢嘎。討論後決定選擇第一條路線。這條路並非沒有危險,河對岸就有解放軍駐地,即八一農場,但是相對而言危險比較小,就算被解放軍發現,他們也得先過河才有可能攔截;即便驚動了民眾,大批人馬過河亦非易事。
人員、時間、路線選定之後,接下來就是具體細節的籌劃。噶廈將此事交由帕拉辦理。帕拉和庫松代本朋措扎西詳細討論了離開羅布林卡的細節,決定由朋措扎西安排達賴喇嘛的護送和警衛,功德林札薩和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負責達賴喇嘛一路的安全,還研究了達賴喇嘛家人的出走方案。
所有的安排必須在不到半天的時間內完成。
代理噶倫柳霞、大秘書土登降秋、布達拉宮的代表曾諄‧羅桑頓珠等人去布達拉宮的寶庫,取出大金磚1塊、象牌金幣50枚、西藏金幣40枚、金螃蟹2只、金鐘1只、印度盧比141,267餘盾,作為路費。
功德林札薩找到協助看守北面的丹巴索巴,囑咐他保密,然後指示他去準備幾匹好馬。經過些許周折,丹巴索巴從羅布林卡馬廄總管處得到5匹馬,但是無法弄到適合的鞍具。
為了避免引起懷疑,噶廈和羅布林卡馬廄的馬匹都不能用,將幾十匹馬送過拉薩河目標也太大,因此功德林札薩指示他的管家,到拉薩河南岸的功德林察格莊園準備馬匹。
帕拉通知達賴喇嘛的私人廚師攜帶廚具和餐具去然馬崗,並頭頂佛像發誓,不將此事透露給任何人。
貢嘎桑天的小隊得到消息,要他們晚上到然馬崗等待。天黑後,他們離開哲蚌寺附近的隱蔽處,潛伏在然馬崗一帶。
朋措扎西找到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通知他安排一些士兵持精良武器等在河邊,並在渡口的左右,以及兩邊的路上安排第六代本的士兵警衛。他還指示第四代本多卡色‧索南多杰和警衛營如本索南扎西,次日夜晚帶領警衛營100多名年輕力壯的士兵作後衛,以防解放軍追擊。也就是說,第一代本,即達賴喇嘛警衛團,並沒有擔任出走時的安全防衛。朋措扎西將守護羅布林卡的責任交給警衛團如本色新‧洛桑頓珠。但警衛團如本色新‧洛桑頓珠回憶文章中,這一情節有些出入:
3月8日(按:原文如此)下午拉薩時間八時許,代本朋措扎西十分緊張地來到營部,把如本、甲本們叫到貢布康說:「今天有重要話給你們講。為了防止外傳,大家要對神發誓。」大家向眾怙主發誓後,他繼續說:「由於時局的原因,達賴喇嘛坐臥不安,提出暫到外地避難。去後,你們如本、甲本們要把軍營內外事務搞得萬無一失。」……最後他具體布置道:「現在隨行騎兵將去領取所需裝備,準備出發,他們的軍餉請如本、甲本立即提前發給。你們的家眷最好搬到農村去,如果時乖命蹇你們也逃走。」說完就倉促地回羅布林卡寢宮去了。
色新‧洛桑頓珠回憶文章中的日期相當混亂,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那天是藏曆2月初8日,下文中提到「當晚拉薩時間10時許,達賴喇嘛、達賴母親、姊姊次仁卓瑪等及隨從經羅布林卡警衛營部,從日馬崗(按:即然馬崗)逃出拉薩,由於我忙著給隨行騎兵發軍餉,行前未能見上達賴喇嘛」。由此可見,文中的這個「3月8日」顯然是與西曆和藏曆的混淆。文中沒有說明「隨行騎兵」的人數,但透露出達賴喇嘛走時,他們還在領取軍餉,那麼這些人應當是在達賴喇嘛走後才出發的,與朋措扎西回憶錄中所說的「次日夜晚帶領警衛營100多名年輕力壯的士兵作後衛」相符。
傍晚,拉薩時間5點左右,即北京時間約下午7點,帕拉派僧官則康堪穹土登才巴去德吉林印度領事館,給總領事齊巴捎了個口信:「您知道局勢很緊張,說不定達賴喇嘛不得不離開拉薩。我們還會繼續跟中國人談判,如果談不成,除了印度我們別無去處。請向貴國政府通報。」齊巴要求帕拉提供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土登才巴再次去印度領事館,捎去帕拉的答覆:細節尚未決定,一旦離開拉薩就無法與領事館聯絡,因此預作準備。齊巴答應據此通報印度政府。
太陽緩緩西沉,天色越來越暗。白天的混亂終於平靜。
河邊突然傳來幾聲槍響,正在宮內巡視的庫松代本朋措扎西吃了一驚。他看看腕錶,將近10點了,第一批人將要離開羅布林卡。按照預訂計畫,達賴喇嘛的母親和姊姊,也就是朋措扎西的妻子次仁卓瑪將帶著阿里仁波切,假裝去一座尼姑庵,走出羅布林卡南門。朋措扎西快步朝她們的住房走去。
花園裡安詳寧靜,宿鳥歸巢,魚沉水底,綠色經幡在輕風裡拂動。那是個多雲的夜晚,星星時隱時現。羅布林卡牆外的民眾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鑽進帳篷,準備度過又一個難眠之夜。
——转自博客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