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環境對於歷史和思想研究者造成了諸多的困境和挑戰,其中之一就是我們能否爲諸如「文革」、「民主運動思潮」、「九十年代爭鳴」、「當代思想史」沿著官方還是「非官方」所掌握的歷史材料進行嘗試需求一種「客觀性」的敘述和價值的判斷;還是應當如同「盲人摸象」般,在有限可用的材料中尋找某種關聯和詮釋取代先入爲主的價值判斷。
在文革和後文革的思想史探究中,這種問題就更顯得突出。儘管在「文革」研究和後文革時代研究已經有了相對深入的研究和爭論,但是在公共領域的主導性敘述(如「支持」和「否定」文革或改革開放此類的價值判斷)已經成爲主流甚至這種「輝格黨式的歷史闡述」倒過來影響著研究本身。
因此,面對這種困境,我試圖具體地圍繞楊小凱和他《牛鬼蛇神錄》(以下簡稱爲《牛》)等著作爲主要分析對象,以他個人的經歷和思想歷程來管窺這些問題。
在思想史的敘述中究竟有幾個「楊小凱」,是否楊小凱思想的差距,以至於我們不得不作爲「兩個楊小凱」來對於他的前後思想進行分類?
作爲思想史事件的《牛鬼蛇神錄》
事實上,在楊小凱去世後的紀念文章中,就已經呈現了不同立場的人對他的詮釋,「革命者」、「反革命者」、「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異議者」、「憲政主義者」、「經濟學專家」、以及尋求超驗維度的「基督信徒」等。儘管這些標籤所描述的都呈現出了楊小凱某些特定時段的一些特徵,但是卻同樣在「官方」和「非官方」各自暗含的意識形態敘述的立場下,沒有深入探討楊小凱乃至他所處的整個時代處於怎樣一種思想變動和連續性。只有梁捷在《楊小凱的兩張面孔》超越了這種斷裂的、標籤化的敘述框架,指出楊小凱思想的連續性,「小凱一生,只關心大問題,大學問。他能進入經濟學,也正因爲胸中包含著中國發展的大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我的基本觀點是,長久以來,對於文革到當下的思想而言,在「官方」和「非官方」二元主導敘事背後,卻共享著以把握「客觀歷史」爲基礎,試圖建立一種真理性的歷史解釋和價值判斷的衝動,都消除著對於歷史事件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理解。然而,在解讀楊小凱的文本時,我們會發現,在楊小凱對於文革及其後來事情的敘述是不同於這些價值判斷的主導敘述,而是呈現出了複雜性和多樣性。
事實上,《牛》具有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首先對於研究文革和後文革思想史,它提供了一位深度參與到湖南造反派運動的親歷者的見證和反思,最爲難得的是提供了關於看守所、勞改隊和監獄的寶貴歷史材料。此外,與其他類似的文革回憶著作(如王學泰《監獄瑣憶》)非常不同的是,楊小凱的思想立場似乎發生了對立性的巨大轉變,從「無政府主義」、「平等派」、「激進革命者」轉變爲了傾向於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保守派,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很多不知內情但卻知道楊曦光和楊小凱的兩個人的人,絕不會接受他倆是同一個人的『假說』」(頁3)。
這也就延伸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思想史的敘述中究竟有幾個「楊小凱」,是否楊小凱思想的差距,以至於我們不得不作爲「兩個楊小凱」來對於他的前後思想進行分類? 值得注意的是,在《牛》書中的第一章「中國向何處去?」中,甚至楊小凱自己都是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混用的方式來進行論述,在一開始,楊小凱都是以第一人稱論述,而在講述因爲1978年刑滿釋放後無法找到工作而改用自己的乳名時,他寫到「從那以後,楊曦光這個人就在中國消失了,而楊小凱卻……被人知道。(頁4)」這種敘述的特殊性,讓人注意到了一個詮釋學的視閾問題,也就是楊小凱自身的「歷史意識」是如何理解自己,並對於文革中那個「自我」經驗進行敘述和詮釋的問題。
而對於研究者而言,就必須回答這裡中所展現的「兩個楊小凱」之謎,即《牛鬼蛇神錄》這本書究竟是「過去那位楊曦光」的思想還是如今這位「楊小凱」的思想,或者是一種反思性的融合詮釋。這是需要讀者和研究者本身再進一步詮釋和說明的過程。一旦我們閱讀《牛》同時期楊小凱的其他學術著作和隨筆時,會不時發現同樣的思想和文字呈現散落在這些文章之中。
因此我們要處理的一個思想史的問題就是,楊小凱的思想,是否如大多數人甚至他自己曾經說的,是完全的一個斷裂,或者相反,事實上還是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呢。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其實並不是單單爲了理解楊小凱,而是以楊小凱爲例,擴展到一個更爲廣闊的思想史領域,那就是在文革乃至當代,對許多諸如「革命」等主題的理解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來解讀,還是其中具有二元論對立者們所忽視的延續性和複雜性。
他點名指出當時湖南幾位常委以及全國官僚的「權力無限大」,而革命人們完全喪失了權力,大批被投入到「公檢法控制下的監獄」。
楊曦光與《中國向何處去》
楊小凱曾回憶他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簡寫爲《何處去》)一文的背景是他從小受到的教育讓其對革命英雄主義充滿崇拜,然而自己的父母在文革開始就遭到批判被定性爲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也迫使他沒有加入保守的組織「聯動」而是在長沙一中參加了反對派「湘江風雷」。不幸的是,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他作爲造反派被當局關押了一個月,出獄後參加串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醞釀出了這篇文章。
在1968年1月12日,他以署名「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發表了《向何處去》的徵求意見稿,而後刊載於同年3月的(廣州)工革聯印刷系統委員會的《廣印紅旗》上。這篇文章的背景是發生在文革1967年1月和2月之間兩個重大事件。在當時被「左派」稱之爲「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在67年1月,首先在上海,以工人爲主的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黨政機關的權力,並且在1967年2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後由改名爲「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這一事件影響到全國,陸續出現了地方造反派成立革委會奪取行政權力的行動,並且也成爲了各地,特別是湖南、重慶等地大規模武鬥的導火索。
而「二月逆流」則是同年2月,中央層面內部老幹部派與文革派在兩次政治局會議上的權力鬥爭,最終也影響到各地「造反派」和原來黨政機關之間的政治博弈。楊小凱將其描述爲當權派對造反派「採取了最急切的殘酷鎮壓手段」,最後,「財產(生產資料)和權力從革命人們手中被奪回到官僚們手中,」他點名指出當時湖南幾位常委以及全國官僚的「權力無限大」,而革命人們完全喪失了權力,大批被投入到「公檢法控制下的監獄」。楊在這篇大字報中不僅直指周恩來爲「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總代表,用陳伯達和江青的立場來支持自己的觀點,而且也對當時的「革委會」並不徹底的革命性提出了批判。
《何處去》的行文很明顯受到馬克思和毛澤東以及當時大字報風格的影響,整篇文章圍繞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信 「五七指示」所展開。毛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軍隊要成爲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創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
而《何處去》一文,楊小凱將其發揮是毛對於「中華人民公社」的構想,指出這並不是一種空想的烏托邦,而是避免蘇聯修正主義道路的科學。然而《何處去》一文真正與「五七指示」不同的是加入了權力鬥爭和暴力革命的內容,這也是導致楊小凱入獄的直接原因之一。對於楊而言,實現「中華人民公社」首先是要推翻已經形成的官僚機構,讓工農兵都擺脫官僚控制,因此,此時的楊小凱將自己劃歸爲「極左派」,要通過暴力最終建立真正人民自治的公社。
這篇文章中,楊小凱也表達了自己對於革命和改良的理解。在他看來,造反派成了的革委會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是「罷官革命」的產物,「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逶迤曲折地變爲資產階級官僚和幾個陪襯的群衆組織代表人物的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統治,而革命委員會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楊小凱認爲自己所在的「省無聯」造反派儘管是「新生的幼芽」,但是確實群衆的自發組織,並且強調不能夠把「革委會專政當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終目的」,而是提倡一種始終需要進行暴力的不斷革命論。
讓人遺憾的是,楊小凱寫到,隨著張九龍的槍決,「那看不見摸不著的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係也帶到墳墓中去,將一些永世無法找到答案的迷留給人間。
《牛鬼蛇神錄》的革命和反思
楊自己在《牛》一書對於爲什麼寫《何處去》一文的事後反思是,他因爲在當時遭到迫害,「希望找一種理論來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馬列正統理論基礎上合法化,而馬克思關於民主主義的觀點及反特權反迫害的觀點,自然成爲他的思想武器。(頁8)」在這本書中,楊小凱呈現了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對於文革和革命的看法,提供給讀者更多理解文革和革命的視角。
有趣的是,如同楊後期的《中國經濟史筆記》一樣,事實上,這本書中仍舊有他在寫作時期進行經濟學研究的主題,特別是勞動分工(頁134)。楊甚至提到了一些與當下主流敘述甚至文革研究所不同和忽視的觀點與內容。比如,在《聖人君子》一章中,「君子」這位前湖南大學的數學教師陳老師,也是指導楊在監獄中閱讀的老師之一,其政治見解就不同,「他預見毛澤東一死,江青等激進派會與共產黨內的保守派官僚發生衝突。如果激進派成功,中國可能有機會徹底改變共產黨制度,甚至爆發革命。如果共產黨裡的保守派佔上風,中國又會回到蘇聯體制,長時間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機會。(頁140)」而在後來的文章中,楊小凱自己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甚至假設過保守派和江青爲主的激進派進行內閣制衡的思想實驗。
而在描述地下革命家張九龍的故事時,楊小凱寫到,張九龍說「人民反對當局的革命情緒像性衝動漲落一樣有一定的週期,民主國家讓這種衝動不斷地發泄,所以很少能形成革命的形式。而共產黨國家沒有讓革命情緒發泄的通道,這種情緒就會積累起來,形成革命形勢。」 (頁56-57)因此張認爲,這種文革,動亂反而有助於鞏固政權。而楊卻不認同這點,即儘管上層操縱下面的兩派,「但下面的人不也在利用上層的衝突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嗎?……文革中兩派形成的社會背景是智商與當年英國圓顱黨和輝格黨之間的衝突及法國山嶽派與立憲派的衝突非常相像。(頁57-58)」但讓人遺憾的是,楊小凱寫到,隨著張九龍的槍決,「那看不見摸不著的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係也帶到墳墓中去,將一些永世無法找到答案的迷留給人間。(頁60-61)」
還有一個故事則反映了在社會底層,文革也具有著並非意識形態鬥爭而是殘忍報復的層面,楊小凱通過勞改犯扒手向土匪講的故事展現了其野蠻性。在文革期間,由勞教就業人員組成的「長沙青年」此時得到了報復公安幹部的機會,一名叫「三毛伢子」的把曾經審訊他的幹部的眼睛挖去。楊這樣寫道: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驚和不安,因爲我一直認爲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政治衝突是由政治觀點的衝突引起,雖然我比別人更注意這種政治衝突背後的社會矛盾,但我不會想到,對於向土匪的小團體而言,這種根深蒂固的階級仇恨和互相迫害卻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報復。我有時用《雙城記》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運動中民衆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會上層階級對下層民衆的系統暴力迫害引起的,正像法國大革命的殘暴的一面是由當年貴族的殘暴引起的一樣。這位長沙話都講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無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識形態黯然失色。(頁67-68)
而在論述他和保守派的成員毛火兵之間的私人友誼時,楊小凱說到了因爲是對文化革命的幻滅感,「這場曾經是人民的『盛大節日』的革命造反從來沒有給人帶來任何好東西,我的激進的理想主義也早就幻滅,這大概是我們友誼的真正基礎。(頁85)」
楊小凱不僅對於革命本身所帶來的問題進行了反思,實際上也反思了革命者參與革命的動機本身。他在《宋導演》中講述過湖南省話劇團的造反派領袖導演宋紹文的故事,宋因爲牽涉到「省無聯」的案子而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15年。在獄中爲了減刑卻不時出賣獄友,也舉報過楊小凱,差點導致楊的加刑。但是在文革結束被平反後,讓楊小凱奇怪的是,在1979年民主運動中,宋又捲入其中,甚至出謀劃策,楊小凱對此的總結是,」他是有某種追求轟轟烈烈和英雄主義的精神病,正像偷窺狂和露陰癖是精神病一樣。(頁256)」因此,楊小凱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更爲豐富社會圖景,並非簡單二元論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之間的關係,而是複雜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對他人殘忍的相互傷害的社會。事實上,楊小凱也提醒人們即便是參加「革命」的人,動機也並非都是單純,而是懷著各種的利益和動機,甚至也是一種革命的精神病態也可能成爲參加者的動力。正如法國大革命的維尼奧所說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上面的這些描述,實際上也表達出了楊小凱在寫作這本書時,對於革命的理解。在革命的非理性浪潮中,參與其中的人的動機是多樣的,而並非單純革命的目的那樣簡單,甚至在革命意識形態的掩飾下是真實的人的慾望和仇恨。從而這也導致了親歷者楊小凱對於激進革命的一種幻滅。
「我是太渺小的個人主義者,我害怕專制和革命帶給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個不關心功利的歷史學家,我會說,專制制度,革命的歷史地位卻是件比功利遠爲複雜的事情。」
「兩個楊小凱問題」:斷裂還是延續
上面已經提到《牛》一書的特殊性在於,他是楊小凱中年之後成爲專業經濟學家其思想逐漸成熟所寫的一本回憶錄。在流傳的關於楊小凱的文章中,幾乎都將楊小凱分成了楊曦光的左翼激進思想和後期楊小凱的右翼經濟保守主義思想。即便是此時的楊小凱本人也將楊小凱和楊曦光無論是在寫作的敘事上還是政治立場區分了開了,似乎呼應了1990年代開始的「告別革命」以及「思想淡出, 學術凸現」的潮流,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牛》這本書本身,還是在梳理楊小凱中後期所寫的文章和研究論文,楊小凱的「革命意識」的思想並不是一種斷裂和消退,而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呈現了出來。
首先,楊小凱將自己的經濟學體系強調的「角點解」的超邊際分析和勞動分工理論,視爲是一場經濟學的思想「革命」。楊小凱在ARE(《美國經濟評論》)和JPE(《政治經濟學期刊》)等最優秀的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出版過經濟學教科書的專著,他將自己的理論視爲對過去基於邊際理論的新古典經濟學提供了變革。在他的幾本經濟學教科書中,楊小凱在導論中都列舉了哥白尼日心說體系取代托勒密地心說體系的例子,認爲自己試圖做的事情,「同哥白尼和開普勒做過的事情相似。通過恢復專業化和分工問題的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位置。」(《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頁13)。遺憾的是,在楊小凱去世後,近年來主流經濟學已經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實驗經濟學等更爲微觀和實證的基礎上,遠超出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範疇,楊小凱提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範式並沒有如同他期待的那樣產生廣泛的影響力,但是有一點可能肯定,楊小凱在自身的研究中仍舊延續了「革命意識」衝動,期待的不是過去理論上的修正,而是一種顛覆性的革命。這種「革命意識」的不僅延續在了楊小凱所從事的經濟學研究中,實際上在他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中,也呈現出了同樣一種複雜的變化和延續性。
楊小凱大約在1987年前後(寫《牛》一書同時期),寫了一篇文章〈中國政治隨想錄〉(在1999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一次研討會的發言稿《中國憲政的發展》楊小凱也做了類似的發言。),一方面他指出了文革的複雜性而不是簡單的否定或支持,並且延續了上面提到的張九龍的觀點,指出「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 民中培養起強烈的反革命情緒。」事實上不僅沒有改朝換代的可能,相反是鞏固的政治權力,因爲「人民自從大躍進依賴對專制政體的不滿在文革中發泄掉了…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今天利用上層衝突觸發革命的機會比以前要小得多,這是文革的積極後果之一。」與此同時,楊小凱也補充了自己反對革命的原因並不是從歷史角度出發,而是從個人角度,「我對革命和專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從一種功利主義立場出 發,而不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我是太渺小的個人主義者,我害怕專制和革命帶給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個不關心功利的歷史學家,我會說,專制制度,革命的歷史地位卻是件比功利遠爲複雜的事情。」
在1999年楊小凱在一次訪談中(〈革命與反革命及其它〉),他進一步修正了他對於革命的看法:
現在我要修正這個觀點,因爲革命理論也有其合理性。我認爲,有些東西在學術上還沒有定論,你不能輕易地說,反革命的理論就是對,或者革命的理論就是對的。革命對統治者總是一種威脅,沒有這種威脅,政府爲人民服務的承諾就不可信;有威脅,其行爲就不會太離譜。美國憲法明確指出:人民的權利是天賦的,而政府的權利是人民給的。所以美國人普遍認爲:你要統治我們,就必須得到我們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國的彈劾制度,就是人民表達革命權利的一種方法。你是否讀過已故的奧爾森的書,他就有非常深奧的革命理論,認爲一個穩定的秩序會使既得利益者尋租行爲制度化,而革命和動亂卻能打破制度化尋租。美國很多經濟學家都很敬佩奧爾森。他甚至把社會動亂看成一個國家興盛的原因(見他的「國家興衰論」)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難興邦」 論者。
縱觀楊小凱從1990年代到臨終前的文章,除了他引以爲豪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範式外,他所關注的最主要的問題仍舊是革命和社會轉型問題,即如何進行一個社會的轉型和利益分配,以及用什麼樣的手段和方式來進行社會的制度安排。無論是他吸收理解的哈耶克思想,還是在他與薩克斯,胡永泰合作的論文《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以及未出版的《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等都將關注點放到了如何通過如何通過憲政所保障的個人權利,特別是私有產權來作爲自由市場的基礎來保證成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
在不同的文章中,楊小凱已經不再提倡自己年輕時所讚許的「法國大革命」,而是對英國「光榮革命」不吝讚美之詞,他認爲「光榮革命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虛君憲政,議會民主制度使政府對公平的政治遊戲規則和法律制度的承諾成爲可信……」從而杜絕了 「國家機會主義」。
儘管楊小凱對於西方制度的演變和發展所閱讀的經濟學之外的文獻非常有限,大多數都限制在制度經濟學的框架之內,比如對於「光榮革命」的理解主要依賴於諾斯(North Douglass )和 溫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在1989年之後所發表的文章,他也意識到自己作爲經濟學家而不是專業歷史學家的侷限。因此,他會對於自身知識的侷限也有所反思。如上文所見,他會嚴謹地修正自己的觀點,強調只是從自身經驗和個人功利主義的角度對革命抱有了保留的態度,但是他並非完全的否定了革命的意義,而奧爾森的《國家理論》則讓楊小凱看到了革命積極的一面,就是打破無法通過漸進改良形成的長期尋租制度結構。
這些論述都呈現出在「兩個楊小凱」的區分中始終具有著深層的延續性和共同的問題意識和關懷。
在我們這個告別革命,思想淡出,民主制度衰敗的後疫情時代中,也許仍舊是一種爝火不息的召喚。
思想史脈絡中的「兩個楊小凱」詮釋
在面對楊小凱思想表面的對立和內在的連續性中,我們可以放在一個更爲寬闊的思想譜系裡來進行理解。
在「革命」一詞主導中國近現代上百年的時間中,無論是對其趨之若鶩還是避之不及的人,常常都會以二元論的方式,非此即彼地理解「革命」及其附屬的詞語。例如「革命」與「改良」,「啓蒙」與「救亡」、「法國革命」與「英美革命」等等,完全忽視了兩者之間具有的有機聯繫,而不是完全對立的關係,在脫離歷史和文獻語境的情況下,成了各種意識形態和立場之爭,這也成爲了上個世紀90年代思想界喋喋不休的主線。
其次,「兩個楊小凱」背後還涉及到著一個更爲深層的問題。在當代歷史和田野研究中,如何對文本和口述檔案進行選擇和鑑別已經成爲研究者重點討論的問題之一。由於時間性,當事人本身也會從自身當下的背景對於記憶性的材料進行加工和選取。具體到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研究中,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官方檔案可信度和可用性不足或限制的問題,儘管口述歷史和個人回憶錄可以作爲一個補充,但是文本的可靠性和適用性仍舊需要具體的進行討論。
因此研究者不僅需要在官方和非官方多種主導性敘事中進行甄別,還需要在極爲有限的資料中,進行多角度複雜性的呈現,因爲隨著一些檔案和個人淹沒在主導性的歷史敘事和詮釋中時,後來的研究者甚至無法找到可供對話的研究問題,甚至被動的延續佔據公共話語權的主導性敘述的路徑進行討論,從而不僅沒有呈現出歷史和歷史詮釋的多樣性、可對話性和複雜性,而是強化了少數幾種能夠在公共領域允許討論的敘事模式,導致了對真實問題討論的遮蔽。因此,楊小凱的整個思想脈絡的意義不僅是給予我們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可以用的視角和文獻來研究文革和文革後社會和知識史。楊小凱生命中所呈現出來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思想變化中實際上仍舊有同樣的問題意識和精神的探索。
在這裡,我嘗試用阿倫特(註:Hannah Arendt,漢娜 · 鄂蘭)《論革命》中提出的類型來解釋楊小凱思想中的連續性。阿倫特洞見性地區分了革命和解決社會問題兩者之間所具有的不同目標。革命的真正的目標是以自由立國,並且革命是政治崩潰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而革命作爲一個解放問題通過釋放在苦難社會中人的痛苦和憤怒,也會產生出破壞性的力量。因此,革命無法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貧困問題。相反,人們一旦運用革命的政治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反而會導致恐怖,而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絕路。
在這個動態基礎上,阿倫特指出了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真正的不同在於,法國革命一開始就偏離了自由立國的基礎,不得不被歷史包袱中人民的痛苦和無休止的同情所左右,從而釋放出暴力。而美國作爲「新大陸」沒有不平等和社會苦難的歷史包袱,因此,革命的方向始終以自由立國和建立持久制度爲目標。在阿倫特看來,真正解決和緩解社會問題的並非通過革命,而是技術(頁78及其後)。
正如梁捷所指出的,「中國向何處去」作爲一個問題意識而言,無論是對於作爲造反派的楊小凱還是經濟學家的楊小凱,乃至生命晚期皈依基督教的楊小凱都是終身求索的一個問題。因此,「革命」和專業技術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看似矛盾的兩者之間,在楊小凱的一生的思想經歷中卻得到了統一。他始終對自我立場處在一種嚴謹的批判性反思之中,並且不斷地糾正著自己的觀點。楊小凱晚年對於「革命」的理解,儘管保持著警惕和保留,也反對「職業革命家」,而強調需要做一個能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有生存技能的公民,但是楊小凱也和阿倫特一樣,指出了「革命」在歷史中重要的意義和目標,以及對於既定尋租化制度的顛覆。而楊小凱所走的道路,在某種意義上並非告別「革命」,而是在解決「社會問題」但是這兩者背後卻是同一種激情和關懷在推動。
儘管楊小凱離開他所關懷的這個世界已經十多年,中國乃至世界的制度結構和思想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他之前的各種論點和理論是否成立和實現,人們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也許我們可以批評他對於西方世界歷史和社會仍舊持有很多簡單化的理解;也可能好奇,如果他還活著,會對特朗普時代的「憲政危機」和如今憲政——民主的衰落,自由市場所帶來的不平等加劇會有什麼樣的看法;然而,至少我們可以認爲,楊小凱在某種意義上,在我們這個思想貧乏、充斥著意識形態爭論和爭吵喧囂的時代中,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想資源,也值得未來的研究者來進一步詮釋和理解一些我們自身膽怯與刻意忽視的東西,這種力量並非因爲佔有了更多的客觀材料,在期刊上爭取了多少話語權力和引用,而是對我們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批判性反思和詮釋。
當楊小凱在出獄時,他寫到「我心中充滿著對未來的嚮往和不安。但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世人,因爲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頁411)」在我們這個告別革命,思想淡出,民主制度衰敗的後疫情時代中,也許仍舊是一種爝火不息的召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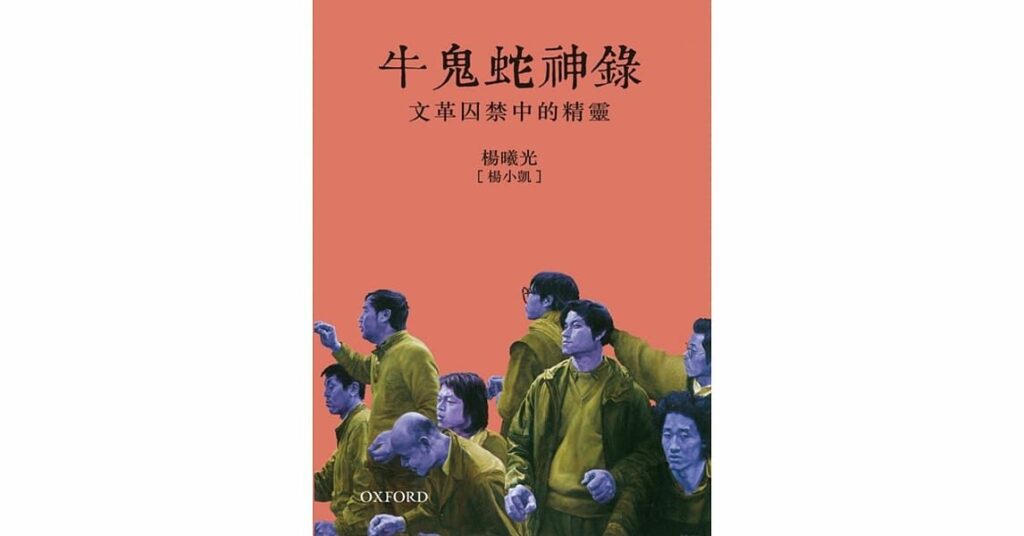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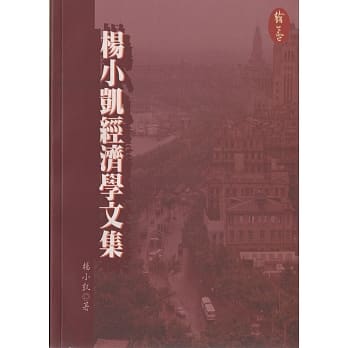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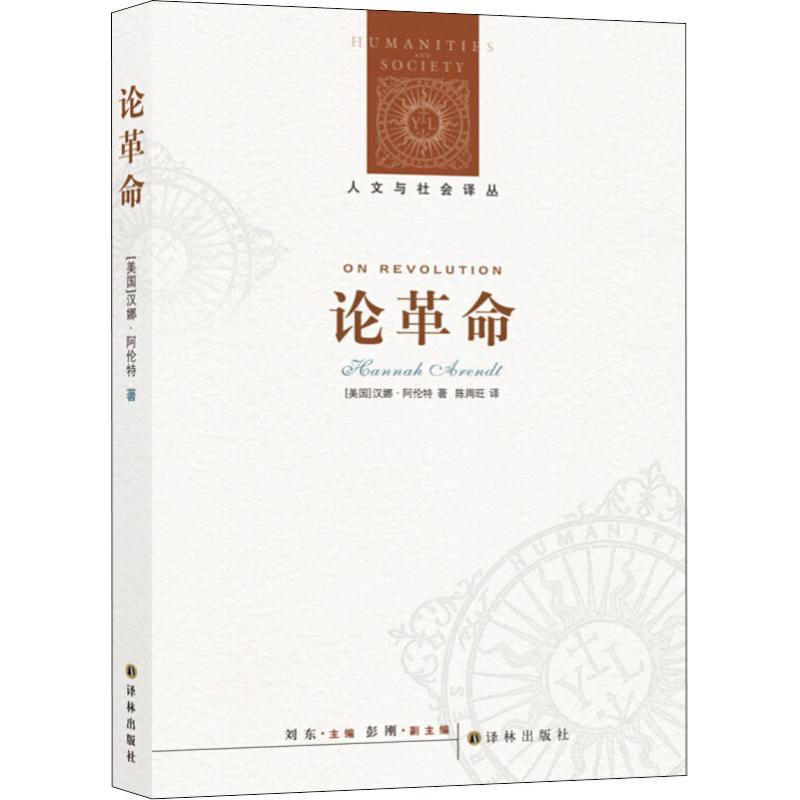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