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薩特發明了自由,又毀掉了自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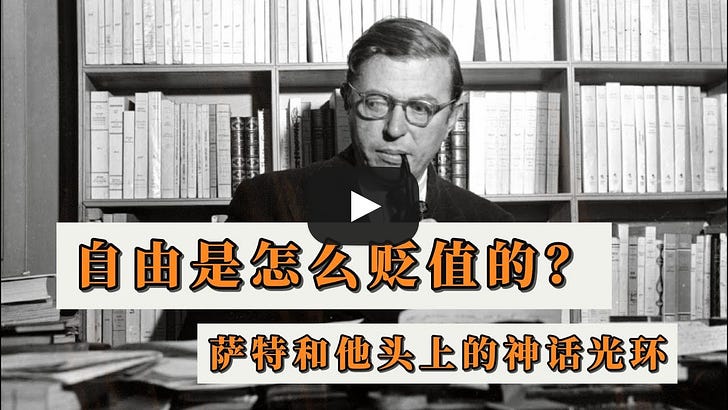
法國女作家弗朗索瓦絲·薩岡在她的小說《你好,憂愁》裡寫了一句離經叛道的話,她說:我打算過一種卑鄙無恥的生活,這是我的理想。
當時薩岡才18歲,就已經因為《你好,憂愁》一舉成名。那時正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尚-保羅·薩特名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不僅薩岡本人就是受到薩特思想洗禮的一代人,她的小說《你好,憂愁》所描繪的離經叛道的生活,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薩岡自己的人生就像她自己的小說一樣放蕩不羈。她隨心所欲地飆車、吸毒、賭博、爛性、揮金如土、自我毀滅。可以說,薩岡和她的小說、以及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很多都是薩特思想的產物。
薩岡最著名的事跡就是迷戀薩特。她還登報公開發表自己寫給薩特的情書,但是直到薩特人生最後兩年,薩岡才有機會見到他。
那時候,薩特已經是風燭殘年,而且雙目失明。薩岡每隔一段時間就上門約他去咖啡館。如果薩特再年輕幾年,她可能還會做薩特的情婦。
薩特的情婦跟風流韻事多到數不過來,但是他影響力實在太大,不管行為有多驚世駭俗,沒有人能阻止他為所欲為,甚至連法國總統戴高樂也要忌憚他三分。
薩特處處跟戴高樂作對,經常高調批評戴高樂。由於薩特公開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有人建議戴高樂逮捕薩特,但是戴高樂說:你總不能把伏爾泰關進監獄把?
法國人經常把18世紀比作是伏爾泰的世紀,也有不少人把20世紀比作薩特的世紀,薩特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那麼,薩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薩特以私生活混亂聞名,但是與許多長相風流倜儻的知識分子不同,薩特不僅身材矮小,還長得很丑。由於小時候生病,他還有一只眼球歪在一邊,看起來很古怪的樣子。
假如我們只讀他的小說、戲劇和哲學書,你會覺得薩特這個人相當枯燥無味,他甚至沒辦法好好講故事。假如他現實中就是這樣的人,顯然不可能有迷倒萬千少女的超凡魅力。
但是如果我們讀他的自傳和私人信件,他就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他變得風趣幽默、妙語迭出,還經常情話連篇、文采飛揚,沒有幾個女人抵擋得住這種魅力攻勢。
薩特其中一個情人叫比安卡·朗布蘭。朗布蘭後來寫了一本書,她說薩特是個情話大師,連講廢話也像做智力體操。郎布蘭是薩特終身伴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學生,郎布蘭在16歲時就被波伏瓦引誘多次發生同性關系。後來波伏瓦還把她轉手介紹給薩特,薩特毫不猶豫就奪走了她的初夜。
比安卡·朗布蘭心懷怨恨地回憶這段畸形的三角關系,她說這種三角關系就像劣質而且油膩的鵝肝,讓人感到惡心。朗布蘭感覺自己作為未成年人遭到了引誘和性剝削,她怨恨薩特和波伏瓦無情地玩弄自己、傷害自己。
像比安卡·朗布蘭這樣的獵豔對象還有很多,其中有不少都是波伏瓦的女學生。波伏瓦很善於利用那些迷戀薩特的女學生。她勾引她們,與她們發生關系,然後又轉手跟薩特分享這些女學生,分享完又將她們拋棄掉。這些女學生有的只留下一些綽號,有的甚至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這樣的事情即使放在現在,也足夠驚世駭俗了。波伏瓦這種雙性戀傾向沒少給她自己帶來麻煩。
二戰初期,薩特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作家,但是也被征召入伍,不久後,薩特所在的法軍部隊就被德軍俘虜。當時波伏瓦在一所女子中學教書,她還寫信向戰俘營裡的薩特炫耀,說她如何如何勾引女學生上床。後來波伏瓦因為與女學生的不道德行為被一些學生家長控告,學校只得將波伏瓦開除。不久波伏瓦還被吊銷教師執照,終身禁止從事教育行業。
波伏瓦跟薩特一樣,幾乎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其中很多都是情書和信件。甚至薩特在德國戰俘營裡也沒有閒著,他每天都在給情婦們寫信,有時候一天寫很多封信。薩特甚至覺得,除了跟情婦們不能見面之外,戰俘營生活挺輕松愉快的。
波伏瓦跟薩特都喜歡在書信裡分享性事。波伏瓦跟薩特一樣情人不斷,她也跟薩特一樣善於講情話。波伏瓦甚至還把跟情人的私生活細節也露骨地寫進小說裡。波伏瓦第一本小說叫《女賓客》,發表於1943年,其中的故事原型就是她自己跟薩特和科薩科耶維奇兩姐妹的四角不倫關系。
當時薩特已經是名人了,這本小說很好地利用了薩特的名氣。但是波伏瓦顯然沒有考慮丑聞會不會影響到科薩科耶維奇兩姐妹,當時科薩科耶維奇兩姐妹因為出演薩特的話劇,已經小有名氣。
不僅如此,波伏瓦還把自己跟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的性事也寫進了小說。這本小說叫《名士風流》,發表於1954年。在小說被翻譯成英語之後,艾格林讀到氣憤不已。
艾格林甚至在美國一家文學雜志上發文,質疑波伏瓦是道德有問題,還是腦子有問題。艾格林是美國作家,起初他對法國文藝界並不熟悉。波伏瓦在訪問美國期間結識艾格林,兩人迅速發展成了情人關系。波伏瓦還把艾格林介紹給薩特,薩特毫不介意他們的關系。
不僅如此,薩特跟波伏瓦還帶著艾格林在巴黎到處參加活動,三人的半公開關系在巴黎社交圈炸開了鍋,當時法國風氣還沒有那麼開放,但是薩特跟波伏瓦一點不理會這些。
有一段時間,也許是為了躲一躲巴黎的流言蜚語,他們三人就結伴出國旅行,去了意大利、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
後來艾格林向波伏瓦求婚,希望波伏瓦跟他去美國。波伏瓦當然不願意離開薩特,而且她跟薩特都發誓永不結婚。波伏瓦跟艾格林分手後,仍然給他寫情書寄到美國去。
等到艾格林與薩特和波伏瓦的關系因為小說事件鬧僵以後,他每當回憶起三人以前的經歷,就感到特別怨恨。艾格林說,薩特和波伏瓦比皮條客跟妓女更懂得怎麼利用別人。這個評論顯然是相當刻薄了。
波伏瓦的人生在許多方面都折射著薩特的人生。二戰結束以後,在波伏瓦結識艾格林之前,薩特在訪問美國期間也發展了不少情婦,其中有一個叫多洛莉絲·凡內蒂,一個為美國政府工作的有夫之婦。不同於薩特的其他情人,凡內蒂更成熟、更有教養、也更有錢,薩特也更愛她。薩特每年都要飛到美國跟凡內蒂生活一段時間,甚至聖誕節也不陪波伏瓦一起過。等波伏瓦也找到一個美國情人之後,兩人就輪番飛美國。有時候是波伏瓦前腳剛離開巴黎,薩特後腳就把凡內蒂接到巴黎。薩特甚至還把他跟波伏瓦共同寫作的作品題詞獻給凡內蒂,這使得波伏瓦跟薩特一度經歷人生中最嚴重的一次關系破裂危機。
凡內蒂是波伏瓦一生都不願意提及的女人,波伏瓦在回憶錄和傳記裡都刻意回避提到這個女人。最後,凡內蒂離了婚來巴黎找薩特,她要求薩特跟自己結婚。這件事情讓薩特非常痛苦,他顯然更愛凡內蒂,但是他不能離開波伏瓦,而且他跟波伏瓦都發誓會永不結婚。
凡內蒂在巴黎窮追不舍,薩特只好跟波伏瓦逃到鄉下去躲了一段時間。我們並不知道多洛莉絲·凡內蒂後來怎麼樣了,總之,她一個人離開了巴黎,但她的人生差不多被毀掉了。
有人將薩特和波伏瓦的開放式夫妻關系追溯到夏爾·傅立葉,因為他們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共同特點就是烏托邦性質。1967年,有一本書被雪藏了將近一個半世紀以後在法國出版,這本書叫《新愛情世界》,作者就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夏爾·傅立葉。
傅立葉在這本書裡猛烈抨擊一夫一妻制度。傅立葉聲稱對愛情的永久忠貞是違背人性的,他甚至還說一夫一妻制度是對女性的絕對奴役。傅立葉甚至將一夫一妻制婚姻比作賣淫,因為這樣的婚姻只會奴役女性,這樣的婚姻最終只會造成對女性的迫害,而且導致女性普遍道德墮落。
傅立葉認為,既然女人給男人戴綠帽子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索性推行多配偶制度。傅立葉與世俗看法非常不同,他認為多配偶制度反而才是對婚姻忠誠的保障。也就是說,多配偶制度不僅解放人的天性,反而還會產生真正的道德。
傅立葉痛斥一夫一妻制度內含排他性的愛情觀念,他指責這種愛情觀念不但會制造獨裁而且愚昧的男人,還會助長不知廉恥而且虛與委蛇的女人。
傅立葉要在他的空想社會裡建立一種開放式的夫妻關系,在這種新型夫妻關系裡,愛就像一種無限增長的社會紐帶,這樣整個社會就構成一個愛情系統,因為只有在性愛平等的情況下,才會有絕對的男女平等和真正的社會平等。但是我們仍然要注意,傅立葉在這裡提到的愛情概念仍然有天主教色彩,其中既包括基於性關系的愛情,也包括社會友愛和博愛等等。
1960年代至1970年代西方國家的婦女解放運動,不僅受到薩特和波伏瓦影響,也受到傅立葉《新愛情世界》的影響,法國尤其如此。當然,也可以說社會環境已經到了可以接受女性平權的年代,這才是傅立葉《新愛情世界》最終等到出版的時代背景。
但是在《新愛情世界》這本書出版以前,薩特跟波伏瓦不見得知道傅立葉對開放性關系有這樣的看法,但是他們跟傅立葉之間仍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在這種有著強烈烏托邦色彩的開放性關系裡,公開透明原則,不僅是忠誠的保障,還可以擺脫嫉妒困擾。但是我們又明顯看到,薩特跟波伏瓦的開放性關系多少有一些反烏托邦的地方。
首先是這種開放性關系並不是那麼和諧。薩特和波伏瓦的開放性關系所牽涉到的其他人就像沒有獨立人格的傀儡,那些人要麼只存在於薩特和波伏瓦的個人傳記中,要麼只存在於經由他們書信或其他形式寫作所呈現出來的想象世界裡,也就是說只存在於他者的凝視之中,並不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
薩特還有無數個情人,那些人甚至都叫不上名字,但不管是誰,那些人在薩特和波伏瓦的開放性關系中,沒有選擇權利、沒有發聲權利,他們甚至不由自主,就像完全沒有自己想法和感受的傀儡跟玩物。
最終,在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開放性關系裡,只有薩特和波伏瓦是自由的,其他人與其說是自由的,不如說是受到了自由的奴役。當然,這裡的自由指的始終是別人的自由,是薩特和波伏瓦獨享自由,是其他人不自由。薩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獄」放在這裡未免有一點諷刺,因為對於其他情人來說,薩特跟波伏瓦才是其他人的「地獄」。
其次是這種開放性關系不僅沒有薩特崇拜者想象那麼和諧,反而還是不道德的,尤其是薩特和波伏瓦並不考慮自己我行我素的行為給別人造成的道德危機。薩特和波伏瓦除了交換男女學生用於濫交之外,還將情人安插在自己的作品裡。薩特的話劇通常都是由他自己的情婦來出演的,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女演員科薩科耶維奇兩姐妹。
薩特和波伏瓦不見得真的尊重科薩科耶維奇兩姐妹,相反,他們嫌棄兩姐妹懶惰、不思進取、沒有什麼思想,甚至沒有什麼恆定的興趣。他們先是引誘姐姐奧爾加·科薩科耶維奇加入他們的混亂性關系,不久後薩特又盯上了奧爾加的妹妹旺達,跟著又把這個妹妹引誘到手。
後來為了擺脫這兩姐妹,薩特又把奧爾加轉手給自己的男學生,而這個男學生還是波伏瓦的長期情人。薩特甚至還把另一位著名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拉進來,加入他自己跟旺達的三角關系。結果不久之後,薩特又與加繆失和翻臉。
為了安撫和補償兩姐妹,薩特就安排她們出演他自己寫的話劇。奧爾加後來公開袒露心聲,她說自己與薩特和波伏瓦的畸形關系對自己造成了嚴重心理傷害。像奧爾加這樣公開站出來的,還有比安卡·朗布蘭和娜塔莉·索羅金,她們都聲稱自己受到了嚴重心理創傷,尤其郎布蘭和索羅金都是波伏瓦教過的女中學生,她們在未成年的時候就遇到這種性剝削。後來在索羅金父母控訴之下,波伏瓦被終身吊銷教師執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波伏瓦被學校開出以後再沒能夠轉到其他地方教書。
在這些畸形關系中,薩特和波伏瓦並不是出於真正的欣賞或者愛情,而是為了滿足自私的情欲,但是被哲學家冠以自由的名義就顯得高尚許多了。
當然,要說甜言蜜語地誘騙,對於薩特來說恐怕是信手拈來,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曾經向多少情婦許諾會離開波伏瓦,跟她們結婚。可以說,薩特要追求的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自由選擇,往往是以情婦們不自由和被迫選擇為代價的。這種代價就像一場空想社會主義實驗造成的後果,其結果就是不但使自由貶值,還使自由變得相當虛無。
最糟糕的還是人們對自由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以至於根本不再相信自由。這是薩特的哲學觀念造成的破壞性影響。1946年,薩特發表哲學著作《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這本書開始糾正其早期的絕對自由觀念。這本書指出,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為「承擔責任」,因為自由和責任密不可分。但是薩特並沒有在實踐這一理念上做出多少改變,他把美國女人多洛莉絲·凡內蒂扔在巴黎,自己跟波伏瓦躲到鄉下去,這無論如何看起來也不像是為自由選擇承擔責任的樣子,那就更不要說那些被他拋棄的情婦,還有出來控訴他的情婦。
當然,你可以說,哲學家並沒有義務要實踐自己的哲學理念;但是如果他自己實踐反而證明了自己哲學理念的荒謬特點,那麼他自己就是自己哲學理念的最好的反駁者。
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特點,甚至也體現在薩特和波伏瓦的政治熱情中,不僅顯得大義凜然、故作高深,甚至還表現得相當不成熟。
薩特跟波伏瓦起初是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二戰初期,德國都已經閃擊波蘭了,薩特還認為戰爭不會波及到法國,可見薩特對於政治的認識並沒有超出他的時代。在戰俘營裡的時候,他想得最多的不是怎麼結束戰爭,也不是國際正義,而是每天給情人寫信和寫小說,他甚至感覺戰俘營裡的日子過得很愉快。這樣的人,你怎麼能指望他從戰俘營出來以後就領導社會思想和抵抗運動?
我們在不少薩特傳記中都看到了這種曖昧表述,就好像薩特從戰俘營一出來就變成了熱衷於政治的劇作家,甚至有人說他的話劇成了法國抵抗運動最強有力的象征。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當時巴黎處在德國軍事佔領之下,薩特能不被逮捕也是奇跡。
二戰結束以後,法國知識界集體左傾,薩特和波伏瓦也不例外。起初薩特跟法國共產黨和蘇聯關系密切,但是薩特不願加入法國共產黨,這讓法國共產黨十分惱火。
1948年薩特話劇《骯髒的手》被認為抹黑了蘇聯和無產階級,尤其是波伏瓦在1949年出版女權主義名著《第二性》之後,蘇聯共產黨對女權主義深惡痛絕,法國共產黨也跟薩特關系緊張起來。
與此同時,羅馬教廷也將波伏瓦《第二性》列為禁書,在此之前,薩特還有一系列著作都被羅馬教廷列為了禁書,他們二人把法國天主教會也得罪遍了。可以說薩特和波伏瓦在法國社會遭到左右夾擊,但是聲名鵲起。
話雖如此,薩特和波伏瓦的左翼立場仍然十分堅定,他們一邊反對美國霸權,一邊反對蘇聯霸權,但是對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卻給予很大熱情,甚至斯大林死後,他們跟蘇聯關系也並沒有那麼惡化。薩特訪問蘇聯期間,蘇聯政府還專門安排克格勃女間諜給他做情婦,但是他可能到死都不知道那個情婦是克格勃女間諜。
1962到1966年期間,薩特還是每年到蘇聯跟那個女間諜幽會。可見薩特本人其實缺少基本政治洞察力,甚至沒有警惕性。
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後,薩特最終跟法國共產黨切割,但是仍然與世界上其他各國共產黨聯絡頻繁。1955年薩特和波伏瓦訪問中國,1960年又訪問古巴,他們顯然受到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盛大歡迎,而且顯然還被這種政治安排迷惑住了,這使得薩特和波伏瓦對中國和古巴的共產主義政權,充滿了不切實際的粉紅色幻想。
後來遇到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薩特依據他自己的哲學個性肯定是要公開表態支持的,結果這一主張又險些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駐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內部成立的反獨立組織,不僅要刺殺戴高樂,也對薩特和波伏瓦下達了追殺令。這樣一來,盡管薩特還沒有被暗殺,但已經被當成了自由斗士,被當成為自由殉道捧上神壇。
1966年,一貫譴責美國干預越南內戰的薩特跟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等人籌建了著名的羅素法庭,用於審判美國的戰爭罪行。薩特甚至要求戴高樂將羅素法庭開在法國,這當即遭到了戴高樂婉拒。
當時法國才剛剛離開北約,如果又開設羅素法庭挑戰美國,無疑會令法國處境相當難堪,但是薩特顯然意識不到這一點。薩特只能求助於瑞典,盡管他1964年才因為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羞辱了瑞典,但是瑞典政府仍然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薩特請求。
等到1968年效仿中國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法國五月運動期間,薩特和波伏瓦驚訝地發現,最激進的法國年輕一代已經開始反對他們了。這時候,他們忽然意識到,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已經過時了。
可以說,薩特和波伏瓦的政治實踐是相當粗淺而且流於表面的。哲學家和作家並不見得具有與其思想相匹配的政治敏銳。單就其將追求自由當成一種政治事業來說,這顯然是不成功的典型。他們不但遭到社會左右夾擊,連年輕世代也拋棄了他們。
這些過於激進的年輕人很多都是受到薩特存在主義哲學自由觀念洗禮,自由對於年輕人來說逐漸變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變得空虛而且沒有意義。後來這成為新一代結構主義思想家批判薩特的一個理論錨點,而薩特更深層次的影響又延續到後現代主義各個思想流派之中,直到意義和價值被拋進了無盡的虛無,盡管薩特並不是這場虛無運動的起點。
——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