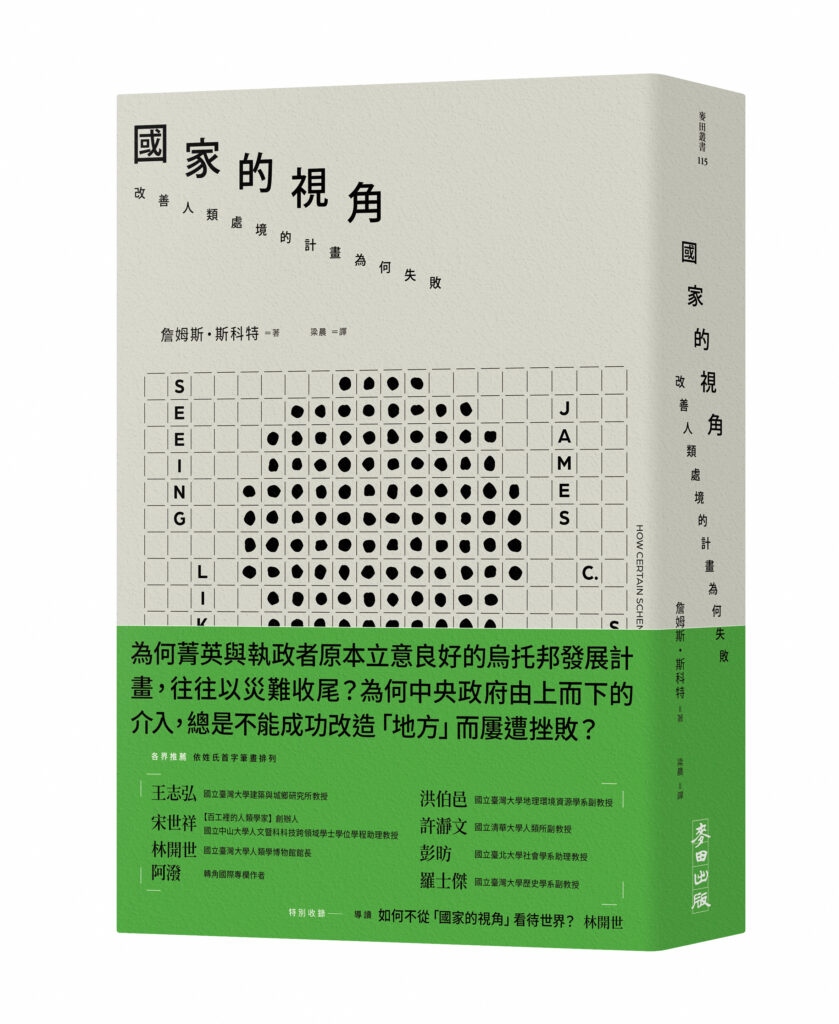
書名:《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3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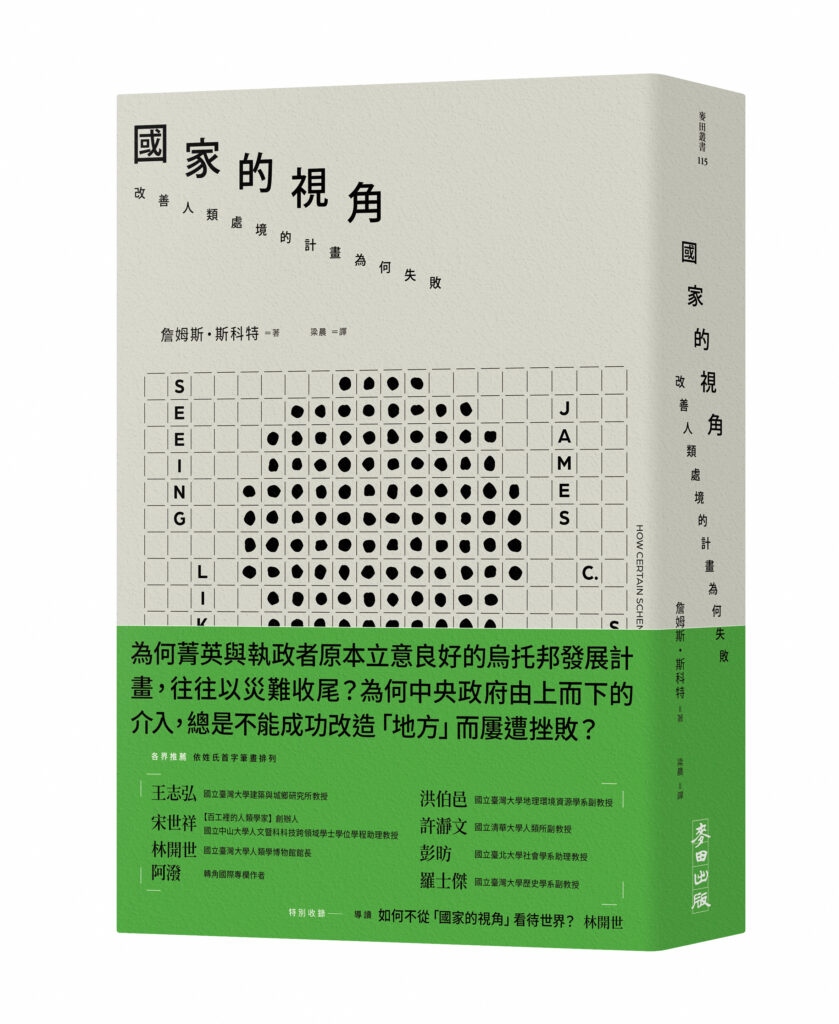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3年6月
第三章 威權主義式的高度現代主義
目前為止,我們所檢視的國家精簡化的工程,其性質都有如地圖。亦即它們是設計來精確地總結大千世界中,對製圖者有直接利益關係的面向,並省略剩下的部分。除非地圖遺漏了使用上不可或缺的訊息,不然抱怨地圖缺乏細緻的差異與細節是毫無意義的。一份城市地圖如果旨在再現每座紅綠燈、道路上的每個坑洞、每棟建築、每座公園中的每個草叢與每棵樹,將會變得與它要描繪的城市一般巨大而複雜。這會讓抽象化與總結等製圖的初衷變得毫無意義。地圖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設計的工具。我們可以評斷其目的是否高尚,或是道德上令人反感,但地圖本身只有符合或不符合其用途的區別。
然而,在每一個案例中,我們已經強調地圖顯而易見的權力,它們能夠轉化以及總結它們描繪的事實。當然,轉化事實的權力並非寄宿在地圖上,而是在掌握在一群人手中,他們擁有決定地圖要使用何種特定視角的權力。當一家私人企業旨在極大化持續性的木材收益、利潤或生產,它會根據這個邏輯對它的世界製圖,並使用它所擁有的權力確保這份地圖的邏輯凌駕一切。在功利主義的精簡化工程上,國家並沒有壟斷權,但國家希望至少能獨占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這也是為何從十七世紀到現在,最具有轉化能力的地圖,其發明者與使用者是社會上最具有權力的機構:國家。
直到最近,國家施加計畫到社會上的能力都受限於野心與實力的侷限。烏托邦本身嚮往經過微調的社會控制,儘管這種對社會控制的抱負,可以追溯到啟蒙時代的思想以及修道院式與軍事般的實踐,但十八世紀的歐洲國家大多都還是一台榨取機器。與前人相比,國家官僚(尤其是在絕對主義時代的國家官僚)的確已經能更詳細地描繪出王國的人口、土地佃租制、生產以及貿易狀況,而且他們也變得更能有效地從鄉村榨取收益、穀物,以及徵兵。但若要將他們的行為稱為絕對主義統治,不得不說有點誇大其實。他們缺乏一致的強制力,既沒有細緻滲透的行政網格,也沒有能採取侵入性更高的社會工程實驗所需的詳細知識。為了充分發揮他們逐漸增長的雄心壯志,他們必須更加狂妄自大,也需要一個可以勝任這項任務的國家機器,以及一個能任由他們宰制的社會。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的西方世界以及二十世紀的其他地方,這些條件才都達成了。
我相信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在諸多國家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悲劇性事件,皆是肇因於三個要素,它們形成特別致命的組合。第一個是嚮往施加行政秩序到自然與社會之上,而這種渴望我們已經在科學林業中看見了,但它被提升到了更加全面且野心勃勃的境界。「高度現代主義」似乎可以適當地形容這種嚮往。高度現代主義有如一種信仰,政治光譜上許多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均將其奉為圭臬。它主要的信使與倡議者是工程師、規劃人員、技術官僚、高級行政官員、建築師、科學家、幻想家中的先鋒派。如果要想像一個高度現代主義者的萬神殿或名人堂,其中幾乎一定會納入亨利.德.聖西蒙(Henri Comte de Saint-Simon)、勒.柯比意(Le Corbusier)、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讓.莫內(Jean Monnet)、伊朗的沙王(the Shah)、大衛.李林塔爾(David Lilienthal)、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I. Lenin)、里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以及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等名字。這群人設想了一項橫掃社會生活所有層面的理性工程,以改善人類的處境。「高度現代主義」作為一種信念,並不是單一政治傾向獨有的性質;我們將會看到,它同時擁有右翼與左翼的變體。造成悲劇的第二個要素,是毫無節制地使用現代國家的權力,作為實現這些設計的工具。第三個要素則是虛弱與衰竭的市民社會,他們缺乏抵抗這些計畫的能力。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欲望;現代國家提供了實行這些欲望的手段;而無力的市民社會有如被夷平的平坦地面,可供建造這些(反)烏托邦。
我們等下很快就會回到高度現代主義的部分。但我想在這裡強調,二十世紀許多由國家發起的巨大人禍,都是對社會具有宏觀與烏托邦計畫的統治者的傑作。我們可以從右派中指認出高度現代主義者的烏托邦主義,其中納粹絕對是個很好辨識的例子。至於南非種族隔離下巨大的社會工程、伊朗沙王的現代化計畫、越南的造村(villagization),以及巨大的後期殖民發展計畫(例如蘇丹的吉濟拉灌溉計畫),都可以被歸在這個旗幟之下。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些規模宏大、國家強制的二十世紀社會工程,往往是出於進步派菁英分子之手,其中多數是革命派。這是為什麼呢?
我相信答案在於取得權力的進步派人士通常有某些特性,他們在上台時帶著對既存社會全面性的批判,而且獲得大眾授權(至少一開始是這樣),讓他們改變現況。這些進步派希望使用權力,為人類的習慣、工作、生活方式、道德行為、世界觀帶來遠大的改變。為了達成目的,他們使用瓦茨拉夫.哈維爾所稱的「整體社會工程的兵工廠」。然而,對烏托邦的嚮往本身並不危險。一如奧斯卡.王爾德所強調的:「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根本不值一哂,因為它忽略了人性總是降落的國度。」對烏托邦的憧憬之所以會出錯,是因為它被對於民主或公民權力毫無承諾的菁英所把持,而他們很可能會使用毫無拘束的國家權力達成這個成就。當屈就於這種烏托邦實驗的社會缺乏頑強抵抗能力時,也是烏托邦願景走向無可救藥的時刻。
那究竟什麼是高度現代主義呢?我們最好將它視為對科學與技術進步信念強而有力(甚至可以說是來勢洶洶)的變體,約莫從一八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信念與在西歐及北美的工業化息息相關。其中心思想是對於以下幾點的高度信心:持續的線性進步、科學與技術知識的發展、生產的擴張、社會秩序的理性設計、人類需求滿足的程度逐漸成長,以及對自然(包括人性)的逐漸掌控,而最後這點與科學對自然法則的理解同步發生。因此,高度現代主義是一個勢不可擋的願景,它關乎如何將技術和科學進步的利益──通常是透過國家──應用到所有人類活動之上。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如果說國家官僚的效益主義敘述(description)傾向透過施展國家權力,將事實硬是向其描述靠攏,那我們可以說高度現代主義的國家,始於對新社會大規模的命令(prescription),而它意圖強加這些命令於新社會之上。
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西方世界,各類型的現代主義者比比皆是,當時的人很難不屬於其中一分子。科學和工業帶來的巨變,怎麼能不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讓人敬畏呢?例如任何一個住在英國曼徹斯特的六十歲人士,在他或她的人生中,會目睹棉花與羊毛紡織業的革命、工廠系統的成長、生產上使用到的蒸汽動力和其他驚人的新穎機械設備、冶金術與交通(尤其是鐵路)上的驚人突破,以及便宜的量產商品的出現。考量到化學、物理、醫學、數學,以及工程的驚人進步,任何有稍稍在關心科學世界的人,無不期待新奇蹟持續到來(例如內燃機引擎與電力)。或許十九世紀前所未見的改變會使許多人陷入貧窮與邊緣化,但這些受難者也會承認某些革命性的事情正在發生。然而到了現代,這一切看起來都十分天真,我們現在遠比過去更清楚認識科學進步的限制與代價,而且也習得了對於任何總體式論述的後現代懷疑主義。但這些新的敏感度忽略了現代主義的預設在我們生活中盛行的程度,同時也特別忽略了一個事實,亦即偉大的熱情和革命的狂妄自大,正是高度現代主義重要的一部分。
發現社會
從描述邁向命令之路,與其說是一種深層心理趨勢偶然的結果,不如說是刻意為之的舉動。從啟蒙運動的觀點來看,成文法的目的不在於反映一群人特有的習慣與實踐,而是要透過將最理性的習俗編入法典,使其成為普世標準,以及打壓最邊緣與野蠻的習俗,以創造出一個文化社群。在王國內建立單一標準的重量與度量衡,其目的不僅僅是促進貿易;這些新的標準意在同時表達與提倡新的文化統一性。早在能為這場文化革命所用的工具存在前,孔多塞(Condorcet)這類的啟蒙時代思想家就在展望使用工具的那一天。他在一七八二年寫道:「這些科學幾乎是我們時代創造出來的,其對象是人類本身,其直接的目標是人類的幸福,這些科學將會享有不亞於物理科學的進步。這個想法是如此的甜美,以至於我們的後代將會在智慧與啟蒙上超越我們,這已不再是幻想。在思考道德科學的本質時,人們將會發現,就像物理科學得立基於觀察事實,道德科學也要遵從相同的方法,獲得同樣準確與精準的語言,達到同樣程度的確定性。」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孔多塞眼裡的光芒成為活躍的烏托邦計畫。之前使用在森林、重量、度量衡、稅收、工廠方面的精簡化與理性化,現在被使用到社會設計整體之上。工業級的社會工程就此誕生。或許工廠跟森林會是由私人企業所規劃,但施加工程到整個社會的野心,幾乎都是由民族國家獨享的計畫。
「國家的角色」這個新概念,代表了十分根本的轉變。在這之前,國家的活動大多都限制在貢獻金錢與權力給最高統治者的人身上,正如科學林業與官房學派的例子所示。而現在國家的中心目的是要改善所有社會成員,提升他們的健康、技巧與教育、壽命、生產力、道德,以及家庭生活,這個想法十分的新穎。當然,舊的國家與新的國家,這兩個概念有直接的連結。改善人民技術、體力、公民道德,以及工作習慣的國家,可以增加其稅收基礎並派出更好的軍隊,任何啟蒙時代的主權實體都可能追求這樣的政策目標。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人民的福祉逐漸不再只被視為增強國力的手段,而是國力本身的目的。
這個轉變的不可或缺的條件,是發現社會作為一個與國家分離、並且能用科學描述的物化(reified)客體。在這方面,國家創造出關於人口的統計知識,例如年紀數據、職業、生育率、識字率、財產所有權、守法程度(以犯罪數據為基礎),讓國家官方可以用盡善盡美的新方式描繪人口,一如科學林業允許林務員能夠小心地描述森林一般。舉例來說,伊恩.哈金解釋有人將自殺率或謀殺率視作一群人口的特徵,所以大家可以像是在討論日常記帳一般,討論每年「花費」在謀殺上的「預算」,儘管沒有人知道這個具體的殺人犯與其受害者是誰。統計事實被精心製作成社會律法,這是從社會的精簡化描述邁向設計與操縱社會的一大步。如果人可以重新形塑自然,設計出更適當的森林,為什麼不重新形塑社會,並創造出更合適的人口呢?
干預的規模可說是毫無止境。社會變成一個物體,而國家可以帶著要讓它臻於完美的眼光,管理並轉化之。一個進步的民族國家,會根據新式道德科學的最先進技術標準來操縱社會。早期國家或多或少原封不動接受既存的社會秩序,當地社會秩序在國家警戒的目光下生生不息,而現在它們史無前例地成為要積極管理的目標。設想一個人工、操縱的社會設計是可能的,設計的基礎不是風俗或是歷史意外,而是根據有意識的、理性、科學的標準。社會秩序的每個角落跟空隙都可能獲得改善:個人衛生、飲食、養育孩童、住宅、姿勢、娛樂、家庭結構,以及最惡名昭彰的人口的基因遺傳。貧困的工人階級往往是科學式社會計畫的第一個適用對象。改善這群人日常生活的計畫隨處可見,受到進步的都市與公共衛生政策廣為宣傳,在典型工廠城鎮與新創立的社福機構中也會制定相關計畫。因為貧困匱乏而可能帶有威脅性的次級人口,包括像是窮人、流浪者、精神病患、罪犯等,可能會成為社會工程最常關照的對象。
作者為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
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農業社會比較發展、霸權與抵抗理論、農民政治、東南亞、階級關係與無政府主義理論等。重要著作有《弱者的武器》(The Weapon of the Weak)、《宰制與抵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等。諳法文、馬來語/印尼語、德文、緬甸語。現為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同時也是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