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被撕裂的社會
誰是「香港人」?
日本人綾香萌生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但綾香的弟弟幾乎沒對反送中運動表現過關心,因為示威而讓公共交通無法使用等諸多不便的事情都令他感到不滿。雖然綾香的弟弟從小就居住在香港,但因為他在日本學校上學,所以跟姊姊不同的是,他連廣東話也不會說。「身分認同」這件事,果然跟語言和生活經驗是息息相關吧。不過,即使不會說廣東話,但對香港有歸屬感、希望繼續在香港居住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人是如何愛上一個特定的地方、對它產生歸屬感的呢?
在法律上,要成為正式的「香港人」(香港居民)、享受與香港市民一樣的權利,就需要取得永久居留權。在香港連續居住七年或以上、遵守繳稅等義務、對香港經濟有一定貢獻的話,就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權,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有了永久居留權,就不需要定期延續工作簽證,也可以自由轉換工作或創業。工作簽證會要求持有人只可以在符合提供簽證資格的公司工作,永久性居民則可以有其他副業。永久性居民在房屋稅也有優惠,如果進行房地產投資,價格上也會更有利。永久性居民也享有於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然而,得到了永久居留權並不代表那些人想永遠居住在香港。二○一九年十二月我到香港考察時,朋友邀請我到一個聚集了日本人的派對;在這些人之中,有的是在香港經營公司超過四十年的人、與外國人在香港結婚的人、在香港養育子女的人、被日本企業派駐到香港工作的人、在香港受僱於香港公司的人、以自由工作者身分生活的人,每個人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在香港生活著。當中很多人都擁有永久居留權。其中一個參與派對的公司老闆,偶然遇上警察在他的辦公室附近驅散示威者。他繪影繪聲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長年住在香港,我從來沒有想過催淚彈會在自己身旁發射、槍戰會在自己周圍發生。警察在我眼前嚴厲要求年輕人、老年人在路旁排成一列,以束線帶之類的東西綁住他們的雙手。香港地鐵站也被破壞,最近才剛剛修復好。」
對於過往一向和平的香港變成了這種被警察鎮壓的環境,許多日本人都有著複雜的感覺。另一方面,在與自己沒有什麼關係的地方有激烈示威、交通被癱瘓,不少人會說覺得困擾,也有人適應不了過分急劇的環境變化正考慮移民。
「在這樣不安定的環境下還帶著小孩,我很苦惱是否應該留在這裡。『不如移民去歐洲吧』之類的建議也在商量中。」
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結婚、跟本地人建立了密切關係的日本人雖然存在,但更多的日本人是不諳廣東話,社群圈內也只有外國人或可以用英文等外語溝通的香港人。
雖然我也是這樣,但在香港,只要懂得買東西、乘搭交通工具時會用上的簡單程度廣東話,日常生活中就幾乎不會感到任何障礙。在開放的都市空間中,各式各樣的語言都被使用,多元的民族、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一起生活,我在香港的時候,幾乎沒有感覺被當作是「格格不入」的人。相對日本,香港可以沒有壓抑感,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因這樣的感覺前來香港的人,在我身邊也有不少。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之中,不少人在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同時,也擁有中國以外的外國國籍。有三十五萬香港人持有在英國殖民地時期發行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也有兩百六十萬香港人符合資格但未仍申領。
除此之外,香港也有具備加拿大、澳洲、美國等各種國籍的人。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華人,在中國政府與香港政府的角度而言算是「中國籍」,只要未申請寫有「中國籍」的香港特區護照,就不會被外國政府視為雙重國籍。這樣的中產或上流階層人士,不時被批評為「離地」(脫離普羅大眾、不知民間疾苦)。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伴隨而來的是,作為香港市民的權利與義務。結果就是,永久性居民可以就政策、輿論、選舉等產生重大影響,但在香港社會有所變動時,也很容易有機會移民到外國。
「香港人加油!」這句口號在反送中運動中頻繁被叫喊著。相比參加者以大學生及高中生為主的雨傘運動,這次的參與者可說遍布各種年齡層、社會階層、職業,一致表明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抗議活動口號的「香港人加油」,當中的「香港人」,所指的到底是誰?又代表著怎樣的意思?或許正因為認知到威脅香港自由的「中國」是「敵人」,而令「香港人」這個身分意識變得更為鮮明吧。
不過,考量香港的現實情況,除了前述有一批隨時可以移民到其他國家的中上階層之外,每日為籌措高昂租金及生活費而苦惱的底層民眾也為數不少,不同社會階層身處的環境有相當大的差異。二○二○年四月,把東京元麻布高級公寓的售價當作百分之一百計算的話,香港同等級別的住宅售價就是百分之二百一十三.四。購買比東京還要貴一倍以上的房子並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事,而近年租金還持續上升。因此,早年已經住在香港的人之間本來已經有很大差距,再加上來自中國新移民中也有富裕與貧窮的人,進一步增加了香港經濟、社會構造的複雜性。
貧富懸殊與貧困化
大專畢業的人佔了香港適齡學生的五成以上,即使大專畢業,也不能奢望可以獲得與上一代一樣的薪資漲幅與向上流動的機會。為了在求職上取得優勢,具有留學歐美經歷、碩士以上的學歷,以及在中國的人際網絡都變得重要。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裡市值排名前十大的公司排序如下:騰訊控股、中國移動、匯豐控股、中國建設銀行、友邦保險、保誠、中國工商銀行、嘉能可Glencore plc、中國平安、中國銀行。市值排名頭十位的公司中,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公司佔了一半以上。我在二○一九年到訪香港大學校園的時候,雖然到處都貼滿企業招聘會的簡介,但我發現不少都是使用簡體字。香港慣用繁體字,以簡體字書寫的招聘簡介,不是顯然打算優待中國學生嗎?我也經常會聽到,在歐美大學畢業的中國人,於香港工作時可以賺到很高的收入。
在香港,可以說每五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窮人。奢侈品牌及珠寶店林立的商場、高級酒店、豪華住宅等呈現出香港的繁榮光景同時,另一方面在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中,也有人住在狹小的「棺材房」。《國家地理雜誌》的報導指出,香港有約二十萬人居住於十平方公尺不到的房間。在只能擺放一張床的空間內,以夾板分隔牆和地板,再鋪上棉被,所有的個人物品只能全部放在上面。這些人生活在沒有窗、濕氣重、蟎蟲滋生的惡劣環境中。
我在香港大學留學的時候,曾經一度離開大學宿舍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其後再回到香港。回港後,我在香港島西面的西環住了大約一年。那個分租公寓與對面大廈的距離近得幾乎觸手可及,從我房間的窗外能夠清晰看見對面大廈租屋房間內的情況。我租下的這個房間每月租金高達六至七萬日幣(約臺幣一萬四至一萬七),但房間狹窄得只容得下一張床,旁邊的細小空間則放了快煮爐,緊鄰的就是廁所與浴室合一的衛浴空間,烹煮食物與如廁的位置之間算是有所分隔。看到我這個從兩房兩廳的正常公寓「隔間」出來的迷你租賃空間,來香港旅行的日本朋友不禁驚訝的說:「虧妳可以在這種地方生活!」
從窗外看到的對面大廈房間裡,只能放得下兩張三層床,卻住滿了六個人。一年之中大部分時間裡,香港的溫度與濕度都很高,住在對面大廈房間的男人,基本上都是赤裸著上半身生活的。本來在床鋪以外,我的房間便沒有足夠的空間,加上徒步十五分鐘就可以到大學上課,所以我白天時間大多在大學研究室中度過。我把大多數的書本和日用品都放在研究室裡,租的房間只是在讀書讀到疲倦時,用來休息和睡覺的地方。
住宅不足下的新移民
我住的隔間房旁,也就是公寓的另外三分之二空間,居住的是一對新移民母子。雖然那名媽媽與香港人結了婚,但因家暴等原因與丈夫分居,或許可能已經離了婚。那名媽媽是福建省福州人,兒子大約四歲,兩人以領社會福利補助維生。那名媽媽說自己是中國的大學畢業,但因為需要照顧年幼的兒子,所以無法在香港工作。現在回想,他們吃飯時偶爾會叫我一起,或者把飯菜分一些給我。
那對母子屏息匿跡過日子,即使有時候社工或者政府的職員來找他們,他們都會假裝不在家。雖然在隔壁房間的我知道他們其實在家,但那名媽媽卻拜託我:「無論妳被問到什麼問題,都請回答『不知道』吧。」社工與政府職員似乎是因為社會福利相關的事而來。曾有人不斷敲門,並在屋外等了很久,可能是那名媽媽的前夫又或者是與他有關的人。然而,那對母子依然一直不做任何回應。
即使都是新移民,但也是有各式各樣背景的人。一直居住在香港的人與新移民之間,於就業與商業經營、社會福利等方面都有互相爭奪資源的情形。我們透過以下對話可以理解。福小姐是本書前言裡提到的人,也是日文學校的經營者,永井先生則是透過福小姐的介紹,在香港經營日本食品生意。
福小姐:「在日本,如果是大阪或鹿兒島的話,三萬日元(約臺幣七千元)就可以租得到一個人住的房子吧。有些香港人會認為,三萬日元就可以租到房子是因為日本施政有效,可以減輕年輕人的生活開支。香港的租金平均是二十萬日元(約臺幣四萬八元),這樣的狀況連香港人也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如果去新界的話,就有很多新移民居住。中小學都有大量中國人的子女入讀,但我們也無可奈何。對社會不滿的情緒就快爆發了。香港每日都在接收一百五十個新移民,在輪流等候公共房屋時,也會有讓他們優先的情況出現。」
永井先生:「香港的土地小,必須透過開山填海來造地。我家在東涌,可以眺望澳門。迪士尼樂園那邊蓋了新橋,也興建了很多新公共房屋區。率先入住的,果然是以中國新移民居多。中小學每個學年都有分配給新移民的學額,香港人完全無法就讀。矛盾的是,雖然公共房屋租金便宜,但私人租屋市場的租金也沒有調降。」
東涌位於香港本島的西邊,是香港最大的島南丫島,搭乘巴士距離香港國際機場大約十五分鐘的車程,東面則是香港迪士尼樂園。
福小姐:「入住公共房屋的所得審查是以平均年收入為基準,但那太嚴格了。大學畢業的起薪很快就會超過那個水平了。那些中國來的人在香港沒有收入,又或是香港本地的老年男性則與來自中國的年輕妻子和小孩一同申請公共房屋,香港年輕人根本無法與這些人競爭。他們為了繳付房租已經夠辛苦了,每個月還要拿出約三、四萬日幣(約臺幣七千至九千元)給父母當家用。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在為生活所苦的同時還會捐款、會去關心西藏的問題,盡全力貫徹自己的信念。我常在想,他們到底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
「每日都接收一百五十人」是指中國當局每日最多可以發出一百五十張「單程證」,讓中國居民到香港定居。香港的入境事務處並沒有「單程證」的審批權,必須接收所有在中國成功申請「單程證」的人。這一百五十人到底是什麼背景也無從得知。
前述的《香港與日本》作者錢俊華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現正於東京大學修讀博士課程。對此他有以下的看法:
「因為新移民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分子,香港的廣東話、繁體字、社會文化,以及自由、法治等價值觀,都希望這群人可以去學習、去理解。香港人也希望他們獲得正確的資訊,深思熟慮後行使他們的投票權。同時,期望可以平等地給予他們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公民』權利。」。關於「香港人已經忍無可忍」這點,錢俊華也提到:「然而我不會再原諒那些不尊重香港的法則、社會規範、價值觀、文化的人。雖然不應使用暴力,但我也會坦率表現自己的反感和憤怒。」(《香港與日本》,頁九十)
認同論述的政治
雖然對待新移民的態度,有時會被形容為歧視或仇恨言論,但錢俊華為對此則是感到「一半高興,一半悲哀」。高興的是,會那樣形容的人背後是承認了香港的主體性,才會分辨中國與香港,並視為歧視。悲哀的是,很多人無視了香港與中國之間壓倒性的實力差距。從中國湧入的大量資金及移民,讓許多香港人重視的文化、語言、法治、制度都被另一套做法所滲透。錢俊華形容「與中國共產黨同化」的情況正在發生中,許多香港人對此已經無法再容忍。
在以上的描述下,日漸鮮明的「香港人」身分意識,果然有著濃厚的「對抗中國」色彩。大部分生活在香港的人,本來是從中國而來,但感到「自己與現在的中國人不同」,也會避開「中國人」的身分。
錢俊華在同一本書中,也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提出了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分析,這項觀點與日本有關。錢俊華認為,作為戰爭記憶的「日本」,連結了香港人的中國民族意識與香港主體意識。歷經日本的佔領、英國的殖民管治,然後是經濟強國的中國,香港總是充滿了外部勢力的影響。「日本」以「局外人」及「民族的仇敵」之角色,若隱若現地出現在香港人的意識當中;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對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形成,確實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雖然日本學校的歷史教育沒有大幅記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美國珍珠港的同時,也入侵香港,並在十八天內攻陷香港,直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為止。日本在香港實行了各種佔領地政策。在日本的佔領下,香港經濟停擺。日本軍方於香港發行軍票,在中國流通的軍票也大舉流入香港,導致通貨膨脹問題。軍票在戰後成了廢紙,當初被迫兌換的人承受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順帶一提,於一九九三年,香港市民就軍票所造成的損失向日本政府尋求賠償,提出民事訴訟,本書第二章介紹過的何俊仁也參與了該訴訟原告的工作。最後,東京地方裁判所認為當時的國際法(海牙公約)原則是不賠償戰爭相關的個人損失,且日本國內也不存在兌換軍票的法律,於是在一九九九年駁回了原告的索賠。
透過美食、動畫等日本文化,現在的香港人對日本抱有好感。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經歷過戰爭世代、對日本佔領時期有負面記憶的香港人,要求交還釣魚台的「保釣運動」也在每個時代積極舉行。在我開始於香港留學的一九九六年,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興建燈塔,引發了「支持保釣」的示威運動。保釣運動領袖、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的創辦人陳毓祥前往釣魚台,並跳入海中游泳以宣示中國領土主權,然而不幸溺水離世。陳毓祥的悼念集會有三萬人出席,他的棺木以五星紅旗覆蓋。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時香港大學的校園內到處都貼滿了寫著「日本人滾出去」的文宣。當時我接受了一份小報的訪問,報導是以一張標題為「(神情憂傷的)日本留學生」大型相片作刊登。
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位於中環交易廣場,這附近的天橋,現在仍然保留了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於二○一七年放置的韓國人、中國人、菲律賓人等的慰安婦銅像。這個保釣行動委員會是由主張中國擁有釣魚台領土主權的社會人士所組成。
前文提及的《香港與日本》作者錢俊華指出,香港的「本土派」以沒有直接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一代為主,正以戰爭記憶作為重新建構香港人共同體和政治動員為核心訴求。「本土派」當中也有提倡「香港獨立」者,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主張屬於政治思想相對激進的組織。對於香港政府企圖引入以中國人的「悲劇」「團結」「勝利」的故事包裝的「官方民族意識」,香港的本土派批評共產黨,並採用與政府完全相反的方法詮釋戰爭相關記憶。雖然「日本」的形象與它的存在間有明顯的差異,但兩者都以與日本相關的記憶作為催化劑,形塑了香港人的認同論述。
作者專門領域為現代中國研究、比較教育社會學。1971年出生於大阪府。大阪外國語大學、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畢業後,取得香港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學位。歷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専門調査員、早稻田大學副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現為同研究科教授。著有《吞噬窮人的國家:來自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警告》(新潮新書、增補版)、共著《超級大國中國的走向:人民奮起)》(東京大學出版社)等多本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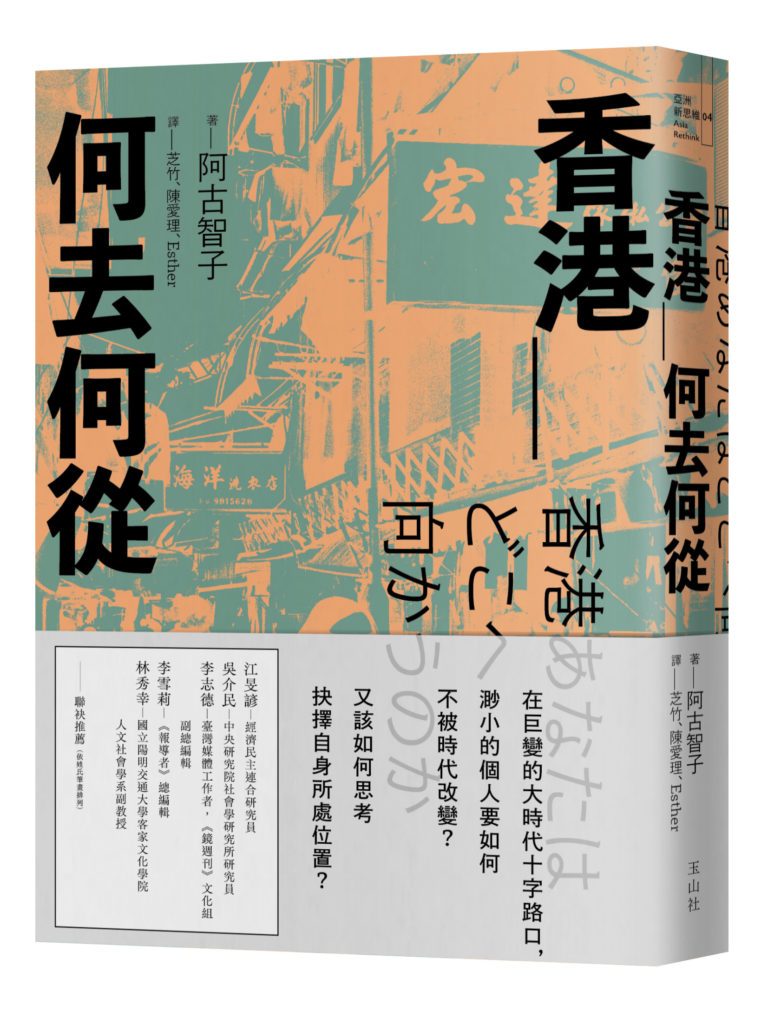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