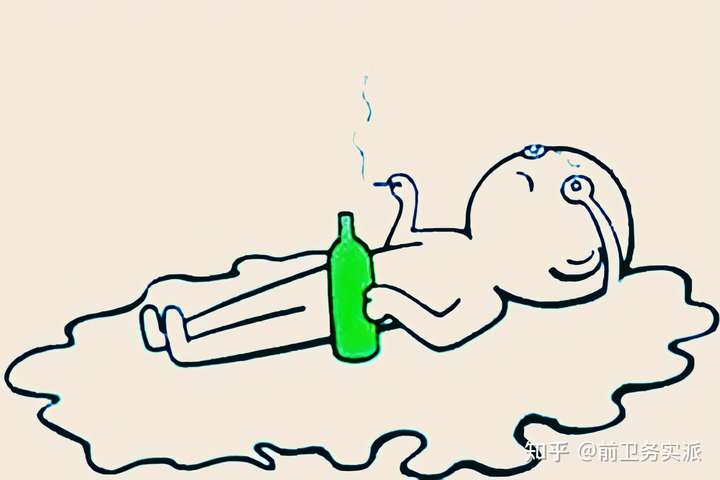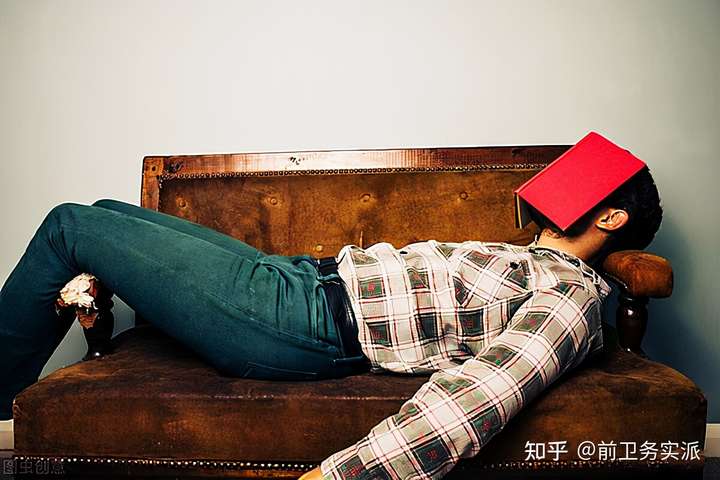习近平的“回乡创业”运动与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
作者:泽西
内容提要:本文对比了习近平的"回乡创业"运动与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揭示了两者在官方叙事、政策逻辑和青年处境上的惊人相似性。文章指出,"回乡创业"表面上倡导农村振兴和青年创业,实质上是掩盖城市就业危机和青年失业率飙升的策略,与毛时代"上山下乡"运动相似,都是在社会危机背景下,将城市青年的去处强制转移到农村。文章通过多个典型案例,揭露了"回乡创业"宣传的虚假性,指出其背后是青年个体权利被漠视、被驱使的现实困境。通过分析两场运动的相同逻辑与不同手段,作者批判了中共体制在危机时刻以青年作为社会稳定筹码的冷酷本质。
"回乡创业"运动:华丽包装下的就业危机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中国各类返乡回乡创业人员总数已超过1200万人。报道引用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的话说,"要用乡村广阔天地的发展机遇来吸引人,用乡村田园宜居的优美环境来留住人,解决好职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让年轻人在农村留得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其实"回乡创业"运动中共早就在暗中布局了,四年前,人社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因为就业危机早就弥漫在中国几百座大中城乡的大街小巷,疫情封控三年后,伴随着企业一波又一波的倒闭,一波又一波的失业者如鸟兽,如无头苍蝇,四处溃散,失魂落魄,失业的焦虑如火如荼,在颓败的城市角落里熊熊燃烧。
于是,官媒报道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不再吝啬版面和时值了。什么卖烧饼年逾百万啦。什么"蘑菇点灯",以蘑菇主题IP农旅融合示范工程,为乡村振兴开辟了创新路径啦。什么"村播"正成为返乡年轻人创业的新路径啦。什么青年返乡创业是传统家庭伦理召唤下的一种选择,追求家庭和睦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回流目标。什么大学生带着对家乡泥土的记忆,从农村考学出去,又回到农村做起"新农人"。但网民们对此普遍很反感。有网友说,"我找不到工作被迫回家,他说我是返乡创业人员。" 有网友一语道破,"你不创业不就增加了失业人数了吗?"
今年两会上,一名来自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赵昭成了官媒热点人物,她大学毕业后回乡养牛,目前饲养肉牛4000多头,实现种养结合,上了头条。但立即遭到一位农村养殖户的质疑,她在抖音上说,现在的牛越来越不值钱,她们村三年前花35000元买了3头牛,现在卖了10头牛只得了32000元,养了三年最后赔了3000元本钱,更别说人工费和饲料费了。她问赵昭养4000头牛是怎么赚的钱?于是,赵昭养牛4000头成了网络敏感词。
公开资料显示, 2015年,赵昭在河南南阳老家成立了一家名叫南阳雅民农牧有限公司,但赵昭的持股比例仅有21%。有网友爆料说,赵昭养牛4000头实际上并不是亲自养的,而是与农户们合作的。一句话,习时代为了掩藏大学生失业危机,制造了一个"回乡创业"运动,刻意把赵昭拔高成一个典型人物,就像当年毛时代刮起"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样,时光飞逝六十年,中共的逻辑和包装还是老样子,六十年未变。
官媒的"回乡创业"神话都是建立在典型案例的神化上。但个案往往具有极强的偶然性、资源性和个体优势,根本无法复制。大多数返乡者面临的现状是,土地流转难,资金支持难,技术落地难,销路打开难。政策文件中许诺的贴息贷款,用地扶持,创业孵化等"红利",真正落地的寥寥无几,即便有几例,那也是应应景,配合宣传,过期作废。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回乡创业"话语,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它假设所有人都"有乡可回",都"有地可种",都"有资源创业",而实际上,今天的农村只剩下留守儿童和孤苦老人,农村早已空心化了,而"返乡潮"正在制造结构性返贫风险。一句话,返乡即返贫。
"返乡潮"正在制造结构性返贫风险
台湾智库谘询委员陈俐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25年预计又有1222万大学生毕业求职,此举可美化失业率啦。"在家附近种点青菜,帮忙种田,创业就不算失业人口,目的在把都市失业人流都灌到农村,本来五个人种一亩田就够,现在硬塞十人去种,这样就人人都有工作了"。
2023年以来,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一路攀升。据北京大学张丹丹教授团队的独立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底青年失业率高达46.5%。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近日在港媒《信报》上撰文指出,中国高校生失业者近三年估计接近三千万,就业率肯定不如官方宣称的56%,平均或低于30%。他提及和内地高校教师交流,他们反应最差的高校就业率仅20%。
近年来,经济大萧条弥漫中国大地,企业倒闭潮卷起漫天失业大潮,潮潮相连。中共却开动所有官媒,对着空气画大饼,齐声合唱"回乡创业",遍寻典型人物,拔高编造唱高调。更可耻的是,中共还把这种严峻的失业困境美化成什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什么大学生返乡创业,技术下沉,人才下沉,激活农村资源,实现自我价值,"新时代新农人"重构乡土中国。中共媒体竭尽华美空洞的大词来粉饰困局,歌颂困局,歌颂灾难,歌颂苦难。
更为扭曲的是,所谓"回乡创业"项目又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数字政绩"和"舆情维稳工具",使得"创业"从自发选择异化为行政工程,这既是对个体的剥夺,也是对创业概念的扭曲。事实上,回乡创业就是几千万大学生先失业于城市,再失业于乡村,穷途末路之际的无奈龟缩,处境之悲摧,心境之悲凉,可以想见,但中共却无视千千万万返乡青年之难之痛之苦,反而选用美好的辞藻予以包装,把丧事当喜事来办,只为了掩盖真相,只为了欺骗来者,欺骗世界。
"回乡创业"现在成了美丽的童话,它搅动的是舆论的泡沫,释放的是体制的焦虑。当城市不能再容纳年轻人,国家就引导他们返回早已空心的乡村,彰显的是中共的无能、冷漠和推卸责任,白云苍狗,天地为证。当"返乡"成为官方指向而不是个体选择时,它就已经不再是希望的出路,而是又一次上山下乡的轮回。
"上山下乡"运动:青春成为维稳的代价和祭品
1968年,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据不完全统计,1968—1978年,全国共有约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名为"响应号召",实为被迫下乡。他们被发配到黑龙江兵团、内蒙古草原、云南边疆、广西山区、贵州高原、江西赣南等地。他们被迫离开城市,离开父母,进入穷乡僻壤,一别十年,命运改写,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这就是毛所说的接受"再教育"。
"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时代最具强制性、结构性、政治操控色彩的人肉磨盘,它是对个体生命尊严的系统性践踏,它制造了大批"半文盲+半农民+无出路"的灰色人群,它摧毁了一代人的青春尊严信念与归属感。无数鲜活的青春被埋葬,无数个体的前程被碾碎,不少人终生未能返城,在异乡终老,他们没有墓志铭,他们的命运淹没在肮脏的滚滚红尘里。
在这里,我们不妨列举几个典型人物。习近平,1969年下放到陕西梁家河,"跳蚤咬得全身是疮",靠父亲关系返京,体现出"有后台可返城"的特权现实。著名导演张艺谋,在陕西插队多年,错过黄金学业期,1978年靠招工返城,卖血买相机,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幸运逃脱者。著名作家韩少功等"知青作家"把这一代经历写入作品,称之为"被牺牲的一代"。著名画家教授陈丹青在演讲中说,"我那代人上山下乡,绝非是理想,而是被流放"。
毛"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动机和目的
"上山下乡"运动是打着"理想"旗号发动的政治运动,用堂皇的"再教育"的口号掩盖权力暴力下的阴暗目的。目的主要有四:一是毛泽东对城市青年造反派力量的恐惧,这是"上山下乡"的真正起点。1968年文革爆发两年后,红卫兵四分五裂,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中。毛决意通过"疏导"方式将造反青年驱离政治核心区域城市,改道农村种田。所谓接受"再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去城市化,去组织化,去政治化的政治大流放。毛认为青年若长期集中在城市,将成为造反力量的潜在温床。他曾警告说,"再不分散,他们就要闹起来了"。
二是城市就业压力山大,文革中大学停办,城市经济停滞,百万中学毕业生"待业在家",构成政治不安定因素。三是文革政治清洗需要"转移视线",避人耳目。四是毛式社会改造工程的延续。自延安时期以来,毛就鼓吹"知识分子改造","劳动改造"。毛式"再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劳动代替教育,瓦解知识青年的独立性;二是以贫下中农的"革命道德"重新洗脑,表面上是"思想改造",实质是剥夺话语权,打断知识更新,去除未来可能的反抗力量。毛不相信知识,也不信任城市,只信仰"服从"与"苦役"。五是权力控制的工具性使用。毛通过"上山下乡"运动,让青年脱离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处于彻底依附与控制状态。
官方宣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自愿"的,但事实是城市户籍被迁出,工龄被断裂,教育被中断,生命被浪费。这场政治运动留下的是一代人的"青春被国家没收"的历史伤痕,造成一代人的断裂记忆与心理创伤。"上山下乡"运动揭示了毛时代的统治逻辑——个人命运服从政治权力的任意摆布。
相隔半个世纪的两场运动,底层逻辑却惊人地相似
从毛泽东的"上山下乡"到习近平的"回乡创业",两场看似风格与动机迥异的官方号召和命令,在逻辑结构上却惊人的相似,都是在"青年多余"的背景下开始启动。当年文革中的红卫兵,今天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都以华丽的外壳遮蔽丑陋的现实。"再教育"与"回乡创业",前者是强迫命令,后者是被迫无奈。本质上都是个体权利被漠视,被驱使,被硬性重构,都提供了"榜样"模板以塑造服从情绪。从"张铁生式知青"到"带货女神村官",个体被刻意神化,国家的溃败被有意掩盖。
当然,"回乡创业"与"上山下乡"也有不同。"回乡创业"不像"上山下乡"那样强制迁户口或政治绑架,它借助的是舆论诱导,资源错配,使"不得不走"看起来像是"自愿回归"。它是一种"结构性推送",不是命令性下放。
"回乡创业"是在市场经济架构下推进的,但正因如此,风险与成本全部由个体承担。没有保障机制,没有退出机制,没有身份恢复路径,失败就是彻底沉没。
通过网络短视频,央媒专题,微博热搜制造了大量"个体逆袭神话",以柔性感动替代刚性灌输,使得"回乡创业"运动更隐蔽,更难被识破。
在两场运动中,青年始终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力逻辑的执行单元。城市不需要他们,乡村无法真正容纳他们。于是国家用"道德语言"给出替代解释:"去农村才能成长","返乡更有意义","艰苦是锤炼",最终的潜台词是:"没有机会就别抱怨,走是你的责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的话表面上温柔,骨子里透露的是深刻的冷漠和邪恶。所谓农村有"机遇",有"宜居",有"职业发展",更主要的是有"社会保障"。你品出其中的寒意了吗?用一句大白话,就是扔出去,自生自灭。这与"上山下乡"时,"不下乡就是逃避改造"的叙事如出一辙。
"上山下乡"是以革命的名义驱逐一代人,"回乡创业"是以创业的名义安抚一代人。一个高举阶级斗争大旗,一个打着振兴乡村的幌子。一个是剥夺户口,一个是剥夺信心。一个是政治性苦役,一个是经济性退场。一个在喊"为人民服务",一个在说"自己找出路"。但无论名字如何变化,本质未变——在国家危机时刻,青年依然是最容易被祭出的稳定筹码。
这就是制度的回响,当它无解于未来,就把你推回原地。当它无法给予希望,就让你"回归大地"。当它说"回乡是出路"时,往往意味着,你已经别无选择。这不是青春的选择,这是中共体制制造的青年命运的轮回。
(作者 泽西,资深财经媒体人,曾供职于中国最大的财经传媒集团20多年,曾撰写过近200万字的深度报道和评论文章。现在干净世界平台和YouTube平台上创建自己的频道"泽西说真相"。主要讲述三大话题:中国问题报告系列话题,毛泽东的幽暗心理解析系列,时政新闻话题系列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