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從一戰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美國外交政策為何總是事與願違?》書摘精選
作者:余杰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決裂,不單單是因為兩人的性格和氣質存在巨大差異,更是因為兩人國際戰略和觀念秩序的根本分歧。自建國以來,美國的外交重點即是大西洋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十九世紀之前,歐洲是現代世界的中心;但二戰開啟了美國的太平洋時代,太平洋開始與大西洋分庭抗禮乃至凌駕其上。
對於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等人而言,從整體上他們要追求從克里姆林宮奪回主動權,並確保西方在歐洲大陸擁有優勢。朝鮮乃至亞洲只是這一總體目標中的一小部分。艾奇遜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決不能允許蘇聯擁有任何機會控制歐洲舊世界的資源以實現其目的。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六十八號決議中指出,由於資源有限,美國的主要關注點是歐洲。美國決策者心中,有明確的利益順序。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一九四七年五月就「美國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對其他國家提供援助」所發出的一份文件中,根據「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將計畫援助的國家排序如下:一、英國;二、法國;三、德國;四、比利時;五、荷蘭;六、奧地利;七、義大利;八、加拿大;九、土耳其;十、希臘;十一、拉丁美洲;十二、西班牙;十三、日本;十四、中國(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十五、朝鮮;十六、菲律賓。
文件指出,首先要對那些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國家提供援助,確保它們保持獨立,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完成經濟復甦。至於中國,文件指出:「共產黨中國一定會成為嚴重問題,即使與蘇聯開戰也是如此,但我們還是有可能通過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在遠東孤立共產主義。」多年之後,回顧這張名單及這段論述,不禁為政策決策者的短視、被思維慣性所束縛而長長歎息。
另一方面,杜魯門和艾奇遜對韓戰是一場「有限戰爭」的設定,對麥克阿瑟來說宛如一道緊箍咒。行政部門拒絕了麥克阿瑟升級戰爭的建議,部分是因為它害怕中美衝突擴大化會讓莫斯科獲利,部分是因為它無法指望得到盟國支持,部分是因為它相信冷戰以及熱戰的決定性戰場在歐洲—這恰恰是麥帥要否定的舊思想。
在戰爭中不尋求完勝,以及忽視共產黨集團在蘇聯老大哥吹起魔笛時翩翩起舞的整體性,是荒謬可笑的做法和想法。這種「自我設限」,歸根結底是出於對蘇聯戰爭能力的恐懼。國際關係學家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指出,美國對蘇聯整體軍事能力的評估,影響了杜魯門政府為追求感知到的利益而採取行動的決心。
杜魯門及其顧問未能看到,二戰之後美國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已發生劇變,美國不單單是大西洋國家,更是太平洋國家。西岸的人口和生產力超過東岸——戰爭期間,有八千萬人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加州成為工業產值第一的州,西部一夜之間實現了工業化。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時,加州奧蘭治郡(Orange County,橙郡)的生產總值超過六百億美元,放在世界各國中足以排在前三十名以內,與奧地利、阿根廷齊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史達林曾企圖按照美國模型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但如後來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模式。
與此同時,戰後亞太地區的重要性超過歐洲,一個日本的能量足以相當於大半個歐洲,還有另一頭亞洲巨象在慢慢爬升—實行民主制度、人口眾多的印度。如果美國全力幫助中國國民黨政府穩定局勢、避免中國走向赤化,日本、印度和中國這三個亞洲大國成為美國在亞太的忠實盟友,美國就不必擔憂蘇聯在亞洲的挑戰了。
麥克阿瑟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看得比杜魯門更深刻,他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提出歐亞並重乃至「亞洲優先」、「亞洲第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麥帥發電報給魏德邁將軍:「在與共產主義的軍事競爭中,將遠東當作一個靜態的、安全的側翼,似乎不再切合實際。」一九四九年,他指責華盛頓「歐洲第一」的思維及相應的「壓制太平洋」傾向,將這些傾向歸結為受馬歇爾及他周圍「聰明年輕人」(「外交賢人」)的影響,歸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理解」東亞問題上的無能,這一失敗源於他們在二戰期間及之後對歐洲事務的專注。他的參謀們準備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華盛頓未能看到蘇聯的攻勢已從歐洲戰場轉移到東亞,這部分是由於在歐洲成功地實施了遏制。但美國的軍事策畫者卻沒有相應地發生變化。
麥帥以直言不諱的口吻指出,長期以來,華盛頓重視歐洲而忽視亞洲,而他本人的觀點在邏輯上源於利益無差別的觀念:「如果我們著手修築一項抵抗政治專制主義入侵的自由防線的總體政策,那麼一條主要戰線與另一條主要戰線將是同等重要的,而對任一戰線的決定性突破,都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整個防線趨於崩潰的危險。」因此,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蘇聯人的勝利;它們為美國安全帶來的威脅,不亞於共產主義在世界其餘地方所進行的擴張。同時,他也批評那些一心只關心自己大陸安全問題的歐洲領導人都是「目光短淺」。
韓戰爆發後,麥克阿瑟在給菲律賓外長羅姆勞(Carlos Romulo)的一封信中指出:「歐洲謎們不明白,亞洲是共產主義勢力的試驗田,如果亞洲整個陷落,那麼不論有無美國的支持,歐洲都不會有一點機會。……他們正在幫歐洲的倒忙,並播下可能導致最終毀滅的種子。要想達到全球和平,亞洲必須和歐洲一樣得到自由。」
後來,麥克阿瑟在國會演講中再度反駁「放棄亞洲」論調:「有人宣稱,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同時保護歐洲和亞洲,還說我們不能分散自己的力量。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說法能比這種表示失敗的說法更妙了。共產主義的威脅是全球性的。它在一個地區的成功,構成對其他地區的毀滅。你在亞洲對共產主義綏靖或投降時,也只能削弱我們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歐洲蔓延所作出的努力。」
這一判斷極具前瞻性——美蘇對峙在歐洲以柏林危機為頂點,但遠未走到戰爭邊緣;而在亞洲,隨後發生了兩場讓美國損失慘重且未能取勝、對民族自信心及國際威望影響甚鉅的戰爭—韓戰和越戰。美國沒有打贏這兩場戰爭,不是國力和軍力無法支撐勝利,而是政府事先缺乏足夠的物質準備和心理韌性。
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亞太(印太)崛起,歐洲衰微,證明了麥帥的遠見卓識。歐洲人仍不願承認這一事實,德國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tler)堅持認為歐洲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美國的重心應當保持在歐洲:「美國在亞太地區沒有如其歐洲盟友那般的夥伴。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是出於共同的利益而與美國結盟的,但無論是這兩國之一還是它們加起來,都遠不能企及歐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分量。」他說得好像歐洲與美國結盟完全是出於「無私」的目的(德國和老歐洲恬不知恥地享受了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免費保護且一毛不拔)。
溫克勒更對日本充滿了種族主義的偏見:「日本與美國之間存有共同利益,但只要這個東亞的天皇之國依舊留有激進民主主義的烙印,依舊對西方的普世主義價值若即若離,那麼它同樣不能像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實質上成為美國的夥伴。」實際上,經過麥克阿瑟改造的日本,在價值觀上比歐洲離美國更近。日本戰後的民主化優於德國,對美國的支持也超過德國——日本支持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德國卻在中美之間三心二意。
川普政府是戰後美國第一個奉行太平洋主義的政府。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論壇發表演講,重申美國未來不會把安全與外交的重心放在歐洲,印太戰略才是美國的重中之重。他強烈建議歐洲應當在自身防衛能力上投入更多,歐洲應該承擔更大的國防責任,而非繼續依賴美國的庇護。
此前一天,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北約位於布魯塞爾的總部表示,美國已經不可能只重視歐洲的防禦,這是戰略上的現實。因為美國首要任務是美國的邊界安全及防禦, 並且美國必須把焦點放在阻止中共在太平洋的擴張戰爭。然而,被左派意識形態和綏靖主義嚴重滲透的歐洲,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世紀變局已經來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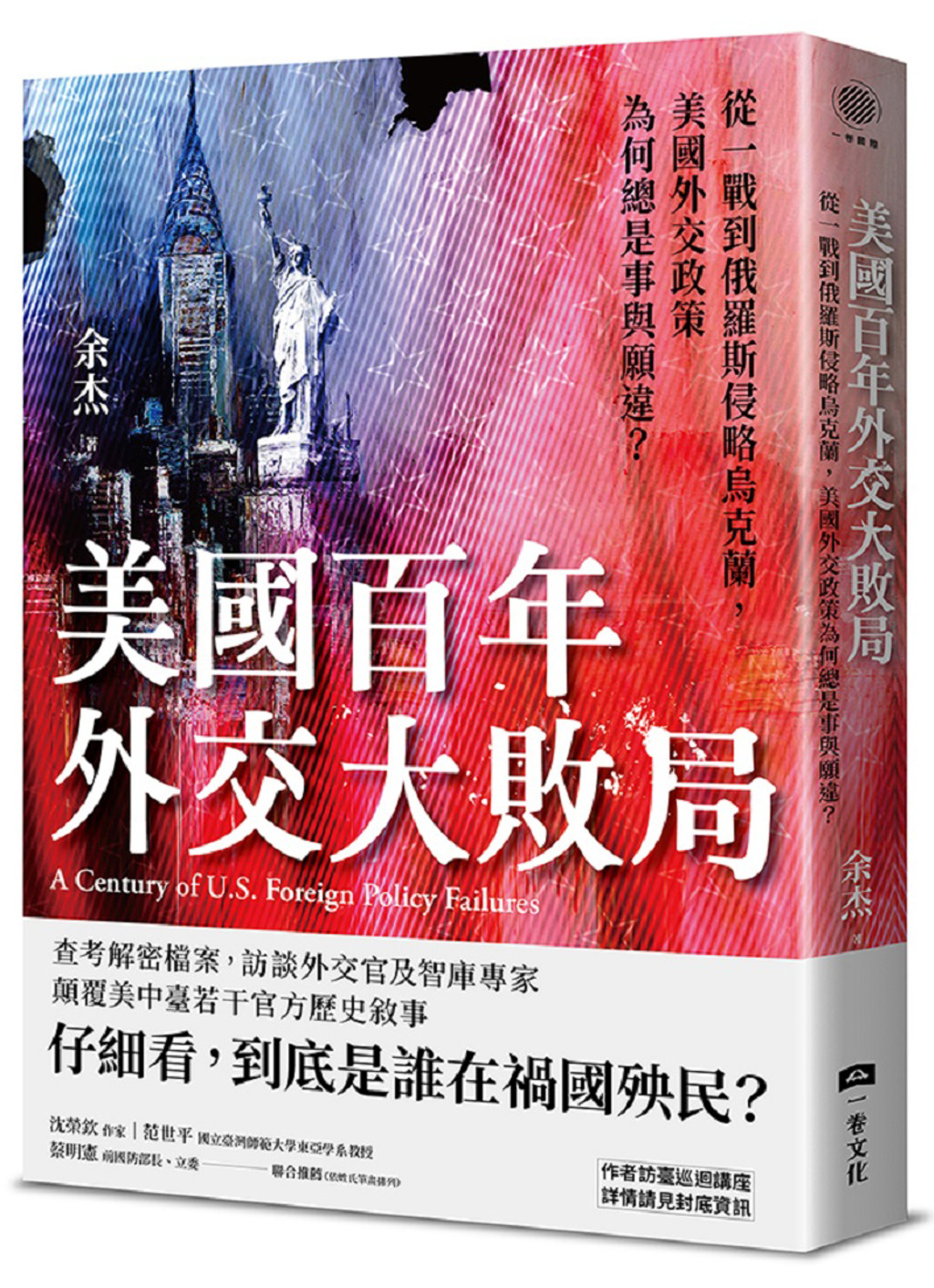
余杰先生的優秀著作,希望盡快出版英文版,並在網絡平台上公開連載,以擴大影響,讓決策者看到,糾正世界方向。
回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