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国涌/文
“美丽岛事件”尚未发生,蒋经国就说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由于外交上的一系列挫折,他遭遇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挑战,为了应对变动的内外局势,缓解台湾岛内民间要求政治参与的压力,他不仅拓宽民间参政的空间,准备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而且批准党外反对派“立法委员”黄信介创办政论月刊《美丽岛》。在蒋经国有意自上而下推动民主进程这个背景下,是年8月《美丽岛》在高雄创刊,短短几个月内不仅发行量水涨船高,而且从南到北建立了十几个办事处,聚集了当时岛内具有相似政治主张的代表人物,不仅言论问政,而且活动频频,实际上成了“没有党名的党”,至少是党的雏形,与以往的一般政论性刊物不同,可以说是一个“美丽岛”政团。当年12月,《美丽岛》出到第4期,发生举世震惊的“美丽岛事件”,由“美丽岛”发起的纪念世界人权日游行,结果酿成暴力冲突,军警与民众双方约200人受伤,万幸的是没有一人死亡,面对突发事件,蒋经国做出的决策,包括抓捕吕秀莲、黄信介、张俊宏、陈菊、施明德、姚嘉文等《美丽岛》重要人物及其他支持者,最后决定将八个主要嫌疑人送军法审判,其他三十多人送司法审判,同时决定公开审判,允许公开报道,努力减少对台湾社会的伤害,并承诺推动民主宪政的进程不会因此止步。“美丽岛”案在媒体众目睽睽之下令举世瞩目,受刑人虽被判刑,却无损他们的人格,许多辩护律师和受刑人家属则由此参与公职竞选,岛上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延缓。“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民主宪政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无论是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受审的党外人士,都没有成为输家,台湾由此结束了全输全赢的政治博弈模式,渐渐迈上双贏、多赢、良性互动的轨道。
一
1979年12月10日上午,国民党在阳明山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蒋经国以党主席身份发表重要讲话:“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话音刚落,高雄当夜即发生“美丽岛事件”。事先,《美丽岛》杂志社申请这一天夜间在高雄举行游行,警备总部担心出事,驳回了这一申请,但知道他们会不顾禁令。情治系统已向蒋经国报告了这个情况,蒋只是指示军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当晚大约9点,目击“美丽岛事件”现场的《台湾时报》采访组副主任李旺台,眼睛里带着催泪瓦斯留下的酸涩感回到报馆。跑警政线的记者已写好了稿子,他发现与自己看到的事实不符,很快重写了一篇,采访主任看完,马上交给了总编辑,总编辑马上跑到社长室,最后社长决定暂时将他的稿子搁在一边,等候国民党主管文宣工作的文工会指示。等了一个小时,居然没有来电,大家都很奇怪,平时小至工厂废气外泄都会来电,今天这件天大的事件却没有指令。为了确认“上面”的意思,报社方面决定继续等,一直过了夜里12点,“上面”还是没有电话。报社在最后一刻决定采用他的稿子,以《镇暴部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为题,并配发了民众与宪警对峙的照片。第二天下午,陈菊还问他:“你看会抓人吗?”他回答:“发生这么大的事,文工会却没有任何指示,这应该代表会有大动作。”
时为文工会主任的楚崧秋有一本口述回忆,其中没有提及“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在第一时间有什么指示,也没有提及文工会最初有什么安排。这与李旺台记忆中他们当夜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是吻合的,可见国民党最高层此时尚未做出明确的安排。
第二天(12月11日),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蒋彦士带着关中、汪敬熙、马纪壮到蒋经国那里报告,与安全局长王永树一起讨论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基本原则、方向,他们依处理的大小范围,提出了甲、乙、丙三个建议案,蒋当场裁示,范围尽量缩小,除了主谋者,其他人尽量不要处理。这是他就“美丽岛事件”做出的最早一个决策。关中记得这个处理范围的建议案可能是安全局提出的。调查局高雄市调处处长高明辉回忆,处理此事的专案小组由国家安全局主导,各情治机关的外勤单位,都奉命搜集滋事分子的名单和资料。当时,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会上很多人发言要求严办,蒋经国的心情也很沉重,起来说:“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他都说,好像我有心事都不说出来;今天我有心事,但我也不便说,你们所说的话,我都有在听,我自已会作一个判断。”要投票选中央常务委员时,蒋经国在休息室,叫了台湾省主席林洋港过去,对他说,“美丽岛事件”发生了,非办人不可,问他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建议主席,国法是一定要执行的,可是栽培一个人才,好比我们种树一样。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些带领的人,大部分也都是我们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建议主席,是不是执法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到我们爱惜人才。”他说自己不敢说“从轻发落”。
蒋经国此时决定抓人,“一则是要在国民党内维持团结一致,也是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13日早上吕秀莲首先被捕,到14日就抓了一百多人,除了施明德当时还在逃,“美丽岛事件”大多数重要参与者都在其中。
当晚大约9点,目击“美丽岛事件”现场的《台湾时报》采访组副主任李旺台,眼睛里带着催泪瓦斯留下的酸涩感回到报馆。跑警政线的记者已写好了稿子,他发现与自己看到的事实不符,很快重写了一篇,采访主任看完,马上交给了总编辑,总编辑马上跑到社长室,最后社长决定暂时将他的稿子搁在一边,等候国民党主管文宣工作的文工会指示。等了一个小时,居然没有来电,大家都很奇怪,平时小至工厂废气外泄都会来电,今天这件天大的事件却没有指令。为了确认“上面”的意思,报社方面决定继续等,一直过了夜里12点,“上面”还是没有电话。报社在最后一刻决定采用他的稿子,以《镇暴部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为题,并配发了民众与宪警对峙的照片。第二天下午,陈菊还问他:“你看会抓人吗?”他回答:“发生这么大的事,文工会却没有任何指示,这应该代表会有大动作。”
时为文工会主任的楚崧秋有一本口述回忆,其中没有提及“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在第一时间有什么指示,也没有提及文工会最初有什么安排。这与李旺台记忆中他们当夜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是吻合的,可见国民党最高层此时尚未做出明确的安排。
第二天(12月11日),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蒋彦士带着关中、汪敬熙、马纪壮到蒋经国那里报告,与安全局长王永树一起讨论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基本原则、方向,他们依处理的大小范围,提出了甲、乙、丙三个建议案,蒋当场裁示,范围尽量缩小,除了主谋者,其他人尽量不要处理。这是他就“美丽岛事件”做出的最早一个决策。关中记得这个处理范围的建议案可能是安全局提出的。调查局高雄市调处处长高明辉回忆,处理此事的专案小组由国家安全局主导,各情治机关的外勤单位,都奉命搜集滋事分子的名单和资料。当时,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会上很多人发言要求严办,蒋经国的心情也很沉重,起来说:“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他都说,好像我有心事都不说出来;今天我有心事,但我也不便说,你们所说的话,我都有在听,我自已会作一个判断。”要投票选中央常务委员时,蒋经国在休息室,叫了台湾省主席林洋港过去,对他说,“美丽岛事件”发生了,非办人不可,问他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建议主席,国法是一定要执行的,可是栽培一个人才,好比我们种树一样。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些带领的人,大部分也都是我们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建议主席,是不是执法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到我们爱惜人才。”他说自己不敢说“从轻发落”。
蒋经国此时决定抓人,“一则是要在国民党内维持团结一致,也是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13日早上吕秀莲首先被捕,到14日就抓了一百多人,除了施明德当时还在逃,“美丽岛事件”大多数重要参与者都在其中。
二
14日早晨8点,行政院长孙运璇奉蒋经国之命召集近20人在中山楼商谈,如何应对此事,参加的有国防、情治、外交、司法等单位主管,及楚崧秋、马纪壮等相关要员。
同日下午4点25分,蒋经国约见楚崧秋,要听听舆情反应。他详细汇报了岛内外新闻言论界的看法和态度,并强调了各方期待公正审判的重要性。两天前,也就是12日下午6点30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邀他见面,询问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自然也是受蒋之命。
17日上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再次约见他,还是谈“美丽岛事件”,进一步询问了各方面反应情形,表达了依法究责的处理原则,并说了这样一番话,不管国家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难,他个人决心是以身许国,以心许民,希望全党同志都能了解他这番态度和心意。
年已古稀、疾病缠身的蒋经国面对这样大的危机与挑战,对亲信下属、旧日学生的这番表白,也透露出他当时压力之大。他将“美丽岛事件”看作“不幸事件”。1980年1月3日下午3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各单位主管参加的党务工作会议上,他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再次重申下列原则:
同日下午4点25分,蒋经国约见楚崧秋,要听听舆情反应。他详细汇报了岛内外新闻言论界的看法和态度,并强调了各方期待公正审判的重要性。两天前,也就是12日下午6点30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邀他见面,询问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自然也是受蒋之命。
17日上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再次约见他,还是谈“美丽岛事件”,进一步询问了各方面反应情形,表达了依法究责的处理原则,并说了这样一番话,不管国家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难,他个人决心是以身许国,以心许民,希望全党同志都能了解他这番态度和心意。
年已古稀、疾病缠身的蒋经国面对这样大的危机与挑战,对亲信下属、旧日学生的这番表白,也透露出他当时压力之大。他将“美丽岛事件”看作“不幸事件”。1980年1月3日下午3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各单位主管参加的党务工作会议上,他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再次重申下列原则:
针对该事件应该是严明而公平地来办,人证、物证要弄清楚;但问题并没有了,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平静下来,因此要加强宣传、组织、社会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才能解决政治方面大幅问题,但我们也绝不会因这不幸事件而放弃反共建国的政治立场,否则就是对不起自己,因此“美丽岛事件”之后,更应开大门、走大路加强工作,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党国生存关头,负责者应该拿出负责的态度来,选举已经在准备,一切依法来办,平静、正常,成败不计。
“美丽岛事件”惊动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作家,害怕酿成第二个“二二八事件”,包括余英时在内,都写信给《纽约时报》,表示“其实受审判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台湾的民主”。他们觉得决策权在蒋经国身上,想找人直接去见他。当时,陈若曦、杜维明、许倬云、余英时、李欧梵、聂华苓、於梨华等27位学者、作家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推陈若曦回台,送到蒋经国手里。陈若曦的《尹县长》等一系列小说引起瞩目,1978年刚获得吴三连基金会首届文艺奖,蒋经国曾推荐过这篇小说,“每个人都应该要看这个书”。
1月7日,陈若曦飞抵台湾。飞机降落时,她还感到恐惧,怕被抓起来。她通过《自立晚报》吴丰山、吴三连找到蒋彦士,提出要见蒋经国,获得同意。她当面对蒋说:“现在人心惶惶,我坐计程车,他们都说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他听到“二二八”三个字,愣了一下,脸色很难看,只说了一句:“一定不会,陈小姐这样子太过虑了。”她把联名信交给他,希望不要扩大化,不要用军法审判。她的意见是,不是叛乱,就不该军法审判。他问:“怎么不是叛乱?如果不是叛乱,请问陈小姐,那这个事件是怎么样的性质?”她冲口而出“那是严重的交通事故”。蒋彦士惊讶地“啊”了一声,站了起来,蒋经国虽也惊讶,却仍不动声色。
这个事件为什么会酿成暴力冲突?到底是“先镇后暴”、“先暴后镇”,还是有“第三只手”?在当时就有争议。陈若曦谈到“暴民打警察”:“那会不会是你们情治单位表演苦肉计?”他听了很生气地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不做这种事。”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11日,《中国时报》报道了蒋经国接见陈若曦,询问生活写作情形的新闻。
时过境迁,多年后,台湾已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被问及:“国防部情报局有没有介入其中?”他只是谨慎地回答:“没有证据显示究竟这么说是真、是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没有掌握内幕资讯,但当时涉及台湾事务的重要官员,相信这种情况不无可能。另一方面,外国观察家和许多照片、录音带证实,是反对派领导人把群众挑激到狂热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领导群众攻击宪兵。”陈若曦后来也认为:“当局是有准备要处理的,你看镇暴车买来第一次使用,但若说是政府预先设个陷阱让群众跳进去,全程导演,我倒不觉得是如此;蒋经国先生坚决否认,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两天后蒋经国即到高雄,指定要坐计程车,想听听计程车司机的看法;并主动安排第二次与陈若曦见面,这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蒋表示,很重视他们这个信,以及他们海外这些人的意见,他会慎重处理,保证这个审判一定是公开的、公平的,还讲了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受冤枉,我就不能够安心。”陈若曦回忆:“后来我对蒋经国这个人还有些佩服,因为他还有求真相的心愿。我从海外回来,带着信要见他的情报相信他早知道了,他还是想亲自听听我怎么说。另外,包括他去高雄坐计程车,这个绝对是他想知道计程车司机的感觉。”
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涉案人的决策大致是,将为首者送军法审判,次要的送司法审判,其他参与者则从轻处置,同时向公众保证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不变。2月1日,警备总部将50名扣押者交保释放,41名交保候传,另有61名在押嫌犯,最后32名送交普通法院,施明德、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8人以叛乱罪送军事法庭审理。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采纳海外学者、作家们的呼吁,但他还是决意要用军法审判,陈若曦回台前正是听说了此意,才会有此建言。
得知要对“美丽岛事件”部分当事人实行军法审判,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跟行政院秘书长周宏涛说:“基于我一贯的主张,我反对用军法审判;因为宪法里规定了,非军人不受军事审判,这写得很清楚。”蒋经国对此不满,对汪道渊说:“梁肃戎怎么反对我采取军法审判呢?”汪回答:“他是好意,因为你如果要同时采取军法和司法审判,你要定个办法划分,不能拿个案送到你这儿来批。你一批要送军法,军法重,可能就是死刑:批要送司法审判,本来应该要死的,却留下了活口。这样不好。”蒋听后表示:“这是对的,他是好意啊。”当时送军法审判的“美丽岛”家属十分紧张,根据动员战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的“二条一”是唯一死刑,他们认为死定了,国民党内的关中等人也是这样认为,蒋经国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决定:“不管你们怎样处理,我不希望看到有死刑。”这句话决定了最后的军法审判结果。获刑最重的施明德被判无期,黄信介20年,其他6人都是12年。
1月7日,陈若曦飞抵台湾。飞机降落时,她还感到恐惧,怕被抓起来。她通过《自立晚报》吴丰山、吴三连找到蒋彦士,提出要见蒋经国,获得同意。她当面对蒋说:“现在人心惶惶,我坐计程车,他们都说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他听到“二二八”三个字,愣了一下,脸色很难看,只说了一句:“一定不会,陈小姐这样子太过虑了。”她把联名信交给他,希望不要扩大化,不要用军法审判。她的意见是,不是叛乱,就不该军法审判。他问:“怎么不是叛乱?如果不是叛乱,请问陈小姐,那这个事件是怎么样的性质?”她冲口而出“那是严重的交通事故”。蒋彦士惊讶地“啊”了一声,站了起来,蒋经国虽也惊讶,却仍不动声色。
这个事件为什么会酿成暴力冲突?到底是“先镇后暴”、“先暴后镇”,还是有“第三只手”?在当时就有争议。陈若曦谈到“暴民打警察”:“那会不会是你们情治单位表演苦肉计?”他听了很生气地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不做这种事。”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11日,《中国时报》报道了蒋经国接见陈若曦,询问生活写作情形的新闻。
时过境迁,多年后,台湾已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被问及:“国防部情报局有没有介入其中?”他只是谨慎地回答:“没有证据显示究竟这么说是真、是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没有掌握内幕资讯,但当时涉及台湾事务的重要官员,相信这种情况不无可能。另一方面,外国观察家和许多照片、录音带证实,是反对派领导人把群众挑激到狂热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领导群众攻击宪兵。”陈若曦后来也认为:“当局是有准备要处理的,你看镇暴车买来第一次使用,但若说是政府预先设个陷阱让群众跳进去,全程导演,我倒不觉得是如此;蒋经国先生坚决否认,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两天后蒋经国即到高雄,指定要坐计程车,想听听计程车司机的看法;并主动安排第二次与陈若曦见面,这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蒋表示,很重视他们这个信,以及他们海外这些人的意见,他会慎重处理,保证这个审判一定是公开的、公平的,还讲了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受冤枉,我就不能够安心。”陈若曦回忆:“后来我对蒋经国这个人还有些佩服,因为他还有求真相的心愿。我从海外回来,带着信要见他的情报相信他早知道了,他还是想亲自听听我怎么说。另外,包括他去高雄坐计程车,这个绝对是他想知道计程车司机的感觉。”
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涉案人的决策大致是,将为首者送军法审判,次要的送司法审判,其他参与者则从轻处置,同时向公众保证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不变。2月1日,警备总部将50名扣押者交保释放,41名交保候传,另有61名在押嫌犯,最后32名送交普通法院,施明德、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8人以叛乱罪送军事法庭审理。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采纳海外学者、作家们的呼吁,但他还是决意要用军法审判,陈若曦回台前正是听说了此意,才会有此建言。
得知要对“美丽岛事件”部分当事人实行军法审判,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跟行政院秘书长周宏涛说:“基于我一贯的主张,我反对用军法审判;因为宪法里规定了,非军人不受军事审判,这写得很清楚。”蒋经国对此不满,对汪道渊说:“梁肃戎怎么反对我采取军法审判呢?”汪回答:“他是好意,因为你如果要同时采取军法和司法审判,你要定个办法划分,不能拿个案送到你这儿来批。你一批要送军法,军法重,可能就是死刑:批要送司法审判,本来应该要死的,却留下了活口。这样不好。”蒋听后表示:“这是对的,他是好意啊。”当时送军法审判的“美丽岛”家属十分紧张,根据动员战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的“二条一”是唯一死刑,他们认为死定了,国民党内的关中等人也是这样认为,蒋经国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决定:“不管你们怎样处理,我不希望看到有死刑。”这句话决定了最后的军法审判结果。获刑最重的施明德被判无期,黄信介20年,其他6人都是12年。
三
3月7日上午10点15分,蒋经国找楚崧秋,主要是关于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国会谈高雄案的意见。3月14日蒋经国再次向他提及处理“美丽岛案”的原则,并不是要以严酷、无情的态度,采取高压手段来对待反对者。当时楚崧秋就觉得,这反映出蒋的基本观念,确是“真心的要以身许国,以心许民”。
外界一直说公开审理的推手是楚崧秋,吕秀莲后来看到他,也在不同场合这样说,他却不愿居其功:“事实上我没有作此主张的身份,而仅是守我分际,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务实可行的建言,所谓‘守其所当言,守其所不得不守’。”他坦言,当时主张公开审判最力的是司法院院长黄少谷,黄是国民党元老,说话有分量,“曾问过我个人看法,当即表示只有审判公开才能将事件的伤害降至最低”。
公开审判的原则当然是蒋经国亲自决定的,也不仅是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1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陈若曦与记者殷允芃的谈话,就以《台湾当局欲公开审判异议分子》为题。这个消息一传出,包括警总发言人在内根本都不知道,就来问,殷允芃答:“是啊,总统就是这样讲的,我们文章也发出去了。”陈若曦回台和《纽约时报》的报道,对他最后决定公开审判都起了作用。
但是,身为文工会主任,对于允许媒体公开报道,包括外国记者采访,显然与楚崧秋有相当的关系。李旺台对新闻局长宋楚瑜邀请国外记者采访“美丽岛”大审不是很理解,主要是不了解这些内情。
当时,情治部门强烈建议,并希望文工会和新闻局配合,限制报道审判内容的新闻篇幅,及岛内记者的采访面。楚崧秋坚持,“既然是公开审判,照规定就应该公开采访,而且中外记者应享有同等权利,才不致贻人口实”。他的这一意见得到蒋经国的认同。不仅因蒋对他信任有加,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恰好与蒋的想法一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也力促台北当局让全世界及台湾人民看清政府对被告的指控。”
3月18日,“美丽岛”一案对八名被告的军法大审开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言论每天都在报纸上大篇幅刊出,几乎是全文。时任《中国时报》采访主任的周天瑞认为,“美丽岛事件”公开审判是一大进步,“是因为国际的关注,再加上楚崧秋这类人比较务实的态度,才有后来的公开审判。而且既然国际人士也能参与公开审判,就不能约束报纸不报道处理”。
关中回忆:“审判期间,记者做笔记,我也做笔记;每天审判回来,我都向秘书长报告,秘书长的书面报告都呈蒋主席。”除了官方途径,蒋经国还有另外的途径了解每天开庭的情况。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沈君山每天参与旁听,晚上回来就向蒋经国报告,讲自己的看法,譬如军法官对被告应该有所尊敬。法庭录影带最后也拿去给蒋看,蒋还会问很多人,像余纪忠、王惕吾等新闻界大佬。
3月21日下午3点45分,蒋经国约楚崧秋谈话,内容包括审判、选举及当前出版界。谈话将结束时,楚顺便提及当时京剧演员郭小庄要上演《感天撼地窦娥冤》,警总下令禁演,认为有为“美丽岛事件”涉案人叫冤之嫌。蒋反问一句:“表演剧团订的场子早在事件发生之前,难道他们演戏的人早就已经预料到‘美丽岛事件’了吗?”蒋的干脆、敏锐令他感慨,蒋是个有自己判断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受下面意见影响的,对于“美丽岛事件”处理的决策过程也是如此。
公开审判、公开采访、翔实报道,台湾民众有机会更客观地了解“美丽岛事件”的真相,更好地理解执政党和党外反对派的分歧和纠葛。对于台湾社会人心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评估,蒋经国敢于这样选择也是需要勇气的。5月10日,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主持的新闻社进行了一项“社会各界对高雄美丽岛暴力事件反应意见之调查研究”,民意调查显示76.1%的受访者认为报纸大量报道政团意见对社会是有利或利多弊少,15.4%的受访者认为是利弊参半,只有4.8%的受访者认为不利或利少弊多。
因为在处理“美丽岛事件”中的态度,出任文工会主任两年半的楚崧秋受到党内攻击,说他是这次“精神污染”制造者之一。当年6月3日下午蒋经国找他谈话,劈头一句:“他们说你自由主义色彩很……”他回答:“教育长知道,我是学政治学的。”当年他是中央大学政治学专业出身,再入中央干部学校,蒋经国是教育长,他们是师生关系。6月20日,蒋经国再度约见,他离开文工会主任的位置,转任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此举对蒋经国而言恐怕也是不得已的,所以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他的建言都在分内,也与蒋的想法接近。
“美丽岛事件”当然是不幸的,数十位当事人受到审判,但是台湾社会没有因此倒退,在蒋经国主导下,政治制度变革的进程没有中断,地方选举继续照常进行,这是蒋经国当时一再重申的,也是他晚年致力的方向。许多“美丽岛”受难人家属和辩护律师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踏上从政之路。《中国时报》记者金惟纯感慨地说:“当然用叛乱的罪名来判是太重了,但是最后没有人被判死刑,还是有一点拿捏分寸。”
不要有死刑,正是蒋经国交代的底线。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记得,他说只要他在位,“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处理“美丽岛事件”,他一方面要应对国民党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台湾社会人心,当时与他有接触的沈君山分析说,“‘美丽岛事件’之后,以蒋经国为主的当局,目的并不是要把党外全部消灭掉,最主要是希望安定”。所以,他才会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闭幕会的讲话中强调力守民主宪政的决心,在1月3日的国民党内会议上再度重申:“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他做出的决策有些出人意料,他上台之后,他的俄苏背景、特工经历,都曾令人不安。陈若曦也说:“我以前觉得他是特务头子,这件事改变一些我对他的评价。”已离开台湾的作家王鼎钧从他的基督教信仰角度提供了一点独特的解释,他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王成勉教授那里得知,《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经国受洗”的具体记录,提及自己为此而感动谢恩,还谈到长达一年和蒋经国共同祷告,最后由其自己决定是否受洗。“他的观念为什么会改变?似非一句台湾人民的压力所能完全解释。既然蒋经国对基督教的投入这么深,岂能船过无痕?”这个线索也可以为我们理解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提供某种参考。
外界一直说公开审理的推手是楚崧秋,吕秀莲后来看到他,也在不同场合这样说,他却不愿居其功:“事实上我没有作此主张的身份,而仅是守我分际,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务实可行的建言,所谓‘守其所当言,守其所不得不守’。”他坦言,当时主张公开审判最力的是司法院院长黄少谷,黄是国民党元老,说话有分量,“曾问过我个人看法,当即表示只有审判公开才能将事件的伤害降至最低”。
公开审判的原则当然是蒋经国亲自决定的,也不仅是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1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陈若曦与记者殷允芃的谈话,就以《台湾当局欲公开审判异议分子》为题。这个消息一传出,包括警总发言人在内根本都不知道,就来问,殷允芃答:“是啊,总统就是这样讲的,我们文章也发出去了。”陈若曦回台和《纽约时报》的报道,对他最后决定公开审判都起了作用。
但是,身为文工会主任,对于允许媒体公开报道,包括外国记者采访,显然与楚崧秋有相当的关系。李旺台对新闻局长宋楚瑜邀请国外记者采访“美丽岛”大审不是很理解,主要是不了解这些内情。
当时,情治部门强烈建议,并希望文工会和新闻局配合,限制报道审判内容的新闻篇幅,及岛内记者的采访面。楚崧秋坚持,“既然是公开审判,照规定就应该公开采访,而且中外记者应享有同等权利,才不致贻人口实”。他的这一意见得到蒋经国的认同。不仅因蒋对他信任有加,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恰好与蒋的想法一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也力促台北当局让全世界及台湾人民看清政府对被告的指控。”
3月18日,“美丽岛”一案对八名被告的军法大审开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言论每天都在报纸上大篇幅刊出,几乎是全文。时任《中国时报》采访主任的周天瑞认为,“美丽岛事件”公开审判是一大进步,“是因为国际的关注,再加上楚崧秋这类人比较务实的态度,才有后来的公开审判。而且既然国际人士也能参与公开审判,就不能约束报纸不报道处理”。
关中回忆:“审判期间,记者做笔记,我也做笔记;每天审判回来,我都向秘书长报告,秘书长的书面报告都呈蒋主席。”除了官方途径,蒋经国还有另外的途径了解每天开庭的情况。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沈君山每天参与旁听,晚上回来就向蒋经国报告,讲自己的看法,譬如军法官对被告应该有所尊敬。法庭录影带最后也拿去给蒋看,蒋还会问很多人,像余纪忠、王惕吾等新闻界大佬。
3月21日下午3点45分,蒋经国约楚崧秋谈话,内容包括审判、选举及当前出版界。谈话将结束时,楚顺便提及当时京剧演员郭小庄要上演《感天撼地窦娥冤》,警总下令禁演,认为有为“美丽岛事件”涉案人叫冤之嫌。蒋反问一句:“表演剧团订的场子早在事件发生之前,难道他们演戏的人早就已经预料到‘美丽岛事件’了吗?”蒋的干脆、敏锐令他感慨,蒋是个有自己判断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受下面意见影响的,对于“美丽岛事件”处理的决策过程也是如此。
公开审判、公开采访、翔实报道,台湾民众有机会更客观地了解“美丽岛事件”的真相,更好地理解执政党和党外反对派的分歧和纠葛。对于台湾社会人心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评估,蒋经国敢于这样选择也是需要勇气的。5月10日,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主持的新闻社进行了一项“社会各界对高雄美丽岛暴力事件反应意见之调查研究”,民意调查显示76.1%的受访者认为报纸大量报道政团意见对社会是有利或利多弊少,15.4%的受访者认为是利弊参半,只有4.8%的受访者认为不利或利少弊多。
因为在处理“美丽岛事件”中的态度,出任文工会主任两年半的楚崧秋受到党内攻击,说他是这次“精神污染”制造者之一。当年6月3日下午蒋经国找他谈话,劈头一句:“他们说你自由主义色彩很……”他回答:“教育长知道,我是学政治学的。”当年他是中央大学政治学专业出身,再入中央干部学校,蒋经国是教育长,他们是师生关系。6月20日,蒋经国再度约见,他离开文工会主任的位置,转任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此举对蒋经国而言恐怕也是不得已的,所以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他的建言都在分内,也与蒋的想法接近。
“美丽岛事件”当然是不幸的,数十位当事人受到审判,但是台湾社会没有因此倒退,在蒋经国主导下,政治制度变革的进程没有中断,地方选举继续照常进行,这是蒋经国当时一再重申的,也是他晚年致力的方向。许多“美丽岛”受难人家属和辩护律师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踏上从政之路。《中国时报》记者金惟纯感慨地说:“当然用叛乱的罪名来判是太重了,但是最后没有人被判死刑,还是有一点拿捏分寸。”
不要有死刑,正是蒋经国交代的底线。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记得,他说只要他在位,“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处理“美丽岛事件”,他一方面要应对国民党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台湾社会人心,当时与他有接触的沈君山分析说,“‘美丽岛事件’之后,以蒋经国为主的当局,目的并不是要把党外全部消灭掉,最主要是希望安定”。所以,他才会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闭幕会的讲话中强调力守民主宪政的决心,在1月3日的国民党内会议上再度重申:“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他做出的决策有些出人意料,他上台之后,他的俄苏背景、特工经历,都曾令人不安。陈若曦也说:“我以前觉得他是特务头子,这件事改变一些我对他的评价。”已离开台湾的作家王鼎钧从他的基督教信仰角度提供了一点独特的解释,他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王成勉教授那里得知,《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经国受洗”的具体记录,提及自己为此而感动谢恩,还谈到长达一年和蒋经国共同祷告,最后由其自己决定是否受洗。“他的观念为什么会改变?似非一句台湾人民的压力所能完全解释。既然蒋经国对基督教的投入这么深,岂能船过无痕?”这个线索也可以为我们理解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提供某种参考。
本文选自《百年寻梦》,傅国涌/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傅国涌作品 点击购买

百年寻梦
厦门大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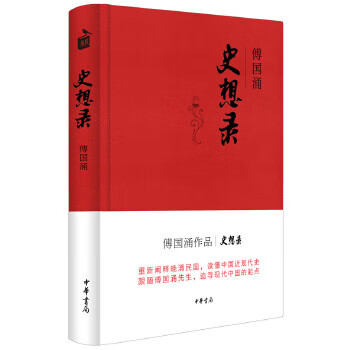
史想录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