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活动的范围非常有限,就我对住家社区的观察而言,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焦虑,更谈不上恐慌了。权威机构现在要求居民的不过是常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最近戴口罩的人多了,但并不是强制性的。有的地方严重一些,我妻弟在纽约,得病10天,自我隔离,现在好了。他太太也有症状,不过比较轻,三四天也就好了。
我每天散步多次,路上的行人都保持6英尺的距离,大家反而更友善了。我如果给一个人让路,不走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去,那个人就会对我挥挥手,说声谢谢。我们有一个单身的女邻居,她是一位舞蹈老师,最近舞蹈课取消了,她没处可去,住的又是一个空间很小的一居室公寓,看上去有些孤独。有一天,她看到我们,说有空可以聊聊天。聊天时,邻居们各搬一张凳子,留开距离,谈的也并不全是疫情。
街上的电线杆上有一些告示,让人感觉到现在是疫情时期,譬如通知社区的居民会议取消了。或者,有谁需要志愿者帮助购买食品,到药房取药,可以打什么电话号码。你随时可以感觉到的是公众社会而不是政府的存在。
疫情期间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和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这场疫情对您最大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可以谈一谈您当下的个体困境吗?
我本人和家庭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改变主要是在生活习惯的方面。譬如我以前每星期要游泳几次,现在改为每日多次散步。我的饮食和睡眠都很正常,所以心态和精神也还正常,心情抑郁的人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开始的,我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能感觉到的不过是一些小小的不方便,图书馆的不便,上书店的不便,游泳的不便,购物、外出就餐的不便,谈不上困境。比起有人家里死了人的,生意做不下去的,失业的,没钱交房租的,一日三餐都有困难的,我所经历的小小不便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我的时间,按照我自己的兴趣阅读、写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想怎么读就这么读。我知道这是一种人生的奢侈。我想,这恐怕是学文科的好处,要是学理工科的,一退休,离开了实验室,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不得不想一辈子在学校当教授。其实,退休是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最好的待遇。我很知足,也很珍惜,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够以平静的心情好好利用时间。我不加入那种互撕互掐的微信群,我不想让任何外在力量,包括疫情在内,搅扰我的心情。
居家隔离期间都看了哪些书,在写什么东西吗?疫情带给您哪些崭新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关于灾难创伤与集体记忆,您写过《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对于这场疫情,您认为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记忆?又应该记住些什么?
我在写作之余,最近看了几本老书,像前哈佛大学教授博克(Sissela Bok)的政治和社会伦理名著《撒谎》(Lying)和《秘密》(Secrets)。我还读了奧布里·塞林科特(Aubrey de Sélincourt)的《希罗多德的世界》(The World of Herodotus),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我教授希罗多德时所用的英译本就是他翻译的,由企鹅出版社出版,是美国许多大学的标准教本。为了查《希罗多德的世界》里的一些细节,我又翻了一下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是以前读过的,但在当下的疫情下再读,体会也就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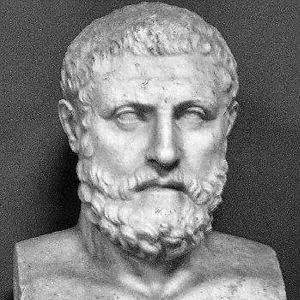
疫情期间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和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这场疫情对您最大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可以谈一谈您当下的个体困境吗?
我本人和家庭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改变主要是在生活习惯的方面。譬如我以前每星期要游泳几次,现在改为每日多次散步。我的饮食和睡眠都很正常,所以心态和精神也还正常,心情抑郁的人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开始的,我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能感觉到的不过是一些小小的不方便,图书馆的不便,上书店的不便,游泳的不便,购物、外出就餐的不便,谈不上困境。比起有人家里死了人的,生意做不下去的,失业的,没钱交房租的,一日三餐都有困难的,我所经历的小小不便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我的时间,按照我自己的兴趣阅读、写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想怎么读就这么读。我知道这是一种人生的奢侈。我想,这恐怕是学文科的好处,要是学理工科的,一退休,离开了实验室,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不得不想一辈子在学校当教授。其实,退休是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最好的待遇。我很知足,也很珍惜,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够以平静的心情好好利用时间。我不加入那种互撕互掐的微信群,我不想让任何外在力量,包括疫情在内,搅扰我的心情。
居家隔离期间都看了哪些书,在写什么东西吗?疫情带给您哪些崭新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关于灾难创伤与集体记忆,您写过《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对于这场疫情,您认为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记忆?又应该记住些什么?
我在写作之余,最近看了几本老书,像前哈佛大学教授博克(Sissela Bok)的政治和社会伦理名著《撒谎》(Lying)和《秘密》(Secrets)。我还读了奧布里·塞林科特(Aubrey de Sélincourt)的《希罗多德的世界》(The World of Herodotus),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我教授希罗多德时所用的英译本就是他翻译的,由企鹅出版社出版,是美国许多大学的标准教本。为了查《希罗多德的世界》里的一些细节,我又翻了一下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是以前读过的,但在当下的疫情下再读,体会也就不同。
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博克的那两本书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品,那时候还不是互联网的时代。前互联网时代的撒谎和秘密,似乎显得比较简单,就像柏拉图时代的叙拉古僭主希亚罗和他的暴政与20世纪的希特勒和纳粹极权相比,便显得相当简单。不过,虽然机制复杂程度或运作方式有所不同,但基本原理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而且对人的危害也更深,更长久了。
英国古典学家塞林科特的《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一本初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老书,许多观点已经显得老旧。但是,不知道老旧的东西,又怎么能看出新观点的新来呢?长期以来,在古希腊历史学家里,希罗多德被视为修昔底德的对立面,修昔底德受到尊崇,因为许多人认为他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更“真实”“客观”“精致”。但是,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人们对希罗多德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认识也有所改变。2009年还出版了了一个Andrea L Purvis的英语新译本《The Landmark Herodotus》, 包括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编者是 Robert B Strassler。
今天,人们重新认识希罗多德的《历史》,因为它体现了一种长期以来一直遭忽视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记录方式。在他的历史中,主题事件(波斯帝国带有必然性的从强盛到衰落)枝枝蔓蔓地似乎不断偏离主题。这曾经遭到诟病,但现在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方式,能引起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特征的思考。
以前,历史学家把希罗多德《历史》里的许多叙述材料当笑话来谈,认为是不真实的无稽之谈,例如,印度有一种掘金的蚂蚁,比狐狸还大,但没有狗大,阿拉伯有一种长着翅膀的蛇,专门危害乳香,还有一种羊,尾巴巨大,牧羊人必须在它的后腿上绑一个木制的小车,它的尾巴才不至于老是托在地上。但是,现在人们意识到,希罗多德运用的是一种有闻必录、记载人事的纪事方式,他记述的事情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他一定会告诉你,希腊人是这么说的,腓尼基人是这么说的。
他所说的历史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信史”,而是“调查发现”的意思。这么一来,读他的“历史”,可以证实的,或者新闻报道的那种“真实”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发生了有人这么认为、这么传说、这么相信的事情。这本身就值得历史学家去记录下来。这正是希罗多德的纪事特征,他说:“我有责任按照我听说的,把事情记录下来,虽然我并不要求自己去相信这样的事情”。他还说:“谁要是觉得这样的事情可信,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解释关于埃及的故事,在我的整个叙述里,我只是按照我从信息来源处听到的记录下来,就这么简单”。
要是有人记录这次的疫情,可以是一种类似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用的是一种有闻必录、记载人事的纪事方式。得病是因为喝了蝙蝠汤,还是因为有美国军人偷偷带进来病毒,这里面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这么说,还有这么多人跟着相信。同样重要的是,因为有人信,有人不信,所以在朋友圈里,甚至在家庭里发生了空前的撕裂。疫病的致死率也许只有2%到4%,但却能让超过20%或40%的人感染上仇恨和敌对的病毒。这些将会成为被记录下来的东西。
希罗多德《历史》可能启发一种崭新的记忆写作方式,它既有一条主线,那就是2019年开始的全球疫情,又有许多出其不意,任何人都难以预料的横生枝节。不断突然出现的事件和插曲令人眼花缭乱,一个谣传、一个谎言、一则新闻、一个发言或表态、一段传闻、一个突然受关注的人物、一份日记、一群人的慷慨激扬,都会在热过几天之后,旋即烟消云散,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例如,有一则关于所谓“美国零号病人”美国女军官Matthew Benassi的传闻,就像巨尾羊和掘金蚂蚁的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后来CNN还专门对各方相关人士做了采访报道,证明完全子虚乌有。
▲4月27日,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对美国“零号病例”当事人玛特捷·贝纳西(Maatje Benassi)进行专访。图为玛特捷与丈夫马特。
这样的事件不管多么失真、荒唐、匪夷所思,都可以成为记忆历史的材料。而且,自2019年以来发生的其他重大“黑天鹅”事件和事件中的事件,以及看似偏离主题的种种插曲也都会进入这个历史叙述之中。
互联网的信息和知识组合特征使得这种既有主线,又枝节横生的记忆历史变得更为可能,互联网提供了维基共笔模式,图文多重链接、专题网页这样的写作方式。如果这次疫情过后,出现一种结合了个人或集体纪实写作的新型历史,那应该是水到渠成、毫不奇怪的事情。这种新型历史的出现甚至可能颠覆当今史学家许多权威的观念,就像网络写作已经和正在颠覆文学人士的所谓权威观念一样。我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关于互联网写作的特征,我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里有所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次疫情中,您最关注的一个事情或者现象、话题是什么?这场疫情暴露出的人类文明、现代文明的最大问题您觉得是什么?
我最关注的是人性在疫情这种极端境遇中的反应和表现。在疫情时期,人性的善良和丑恶都比平时更明显更强烈的表现出来。在美国,有的人家会在门口安放免费的洗手处,还有肥皂或洗手液,供路人使用。很多人都是戴自制的口罩,把医用口罩捐献给医院。但也有囤积口罩想要以此牟利的,警方在一仓库里发现3600副口罩、49.7万副手套以及12756瓶消毒酒精洗手液。这种贪婪的人性恶只是在少数人那里才有表现。
疫情期间的人性丑恶,最典型的就是幸灾乐祸。疫情期间的幸灾乐祸与平时有所不同。平时的幸灾乐祸发生在有可比性的人们之间,如熟人、同事、邻居、同行人士等等。在社会伦理和人际道德中,幸灾乐祸是一种比“妒嫉”更邪乎的“恶”——妒嫉是不乐意见到别人有好事,而幸灾乐祸则是以别人的祸事为乐。叔本华说,妒嫉虽然不好,但却是人之常情,而以别人的不幸为自己快乐则是魔鬼心肠。他认为,幸灾乐祸是人性中非常接近“残忍”的部分。疫情期间的幸灾乐祸主要是通过网络的媒介来表达的。这种狭隘族群意识支配的幸灾乐祸其实是仇恨在作祟,而仇恨是人性恶中最恶的部分。
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恻隐之心,而且以别人的苦难为自己的快乐呢?长期的仇恨教育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互联网的情绪放大作用和回音室效应。这是一种网络时代的群氓和暴民心理,19世纪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中已经有了经典的分析。但他那个时代还没有互联网,互联网时代,一个人每天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铺天盖地的暴力和仇恨,自己马上就有了相同的冲动,而发泄这种冲动又是如此方便,只要手指轻轻扒拉一下,就可以感受到在一个大人群里的那种亢奋和满足。许多人是经不住这样的诱惑的。这种亢奋和毒瘾一样,刺激的计量需要不断增加。
人类的文明建立在人的自我克制之上,野蛮的冲动是自然的,而唯有理性和自我克制才能限制人类野蛮的自然冲动,进入文明的境界。有人说,疫情让人更敏感于人的生存处境,永远徘徊在“没有人是孤岛”与“他人是地狱”之间,人对其他人既需要也排斥。这两种心理趋势其实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脱离群体生活,也没有人能够只是在群体中生活。但是,如果泛泛而谈,这样的话等于废话。问题不在于个人与群体的冲突,而在于那是一个怎样的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有素质、价值观和道德行为标准的差别。
您在《人文的互联网》中探讨了互联网对人类思维、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与改变。那么您对于互联网在这次疫情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怎么看?仅从疫情角度而言,您认为互联网真的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吗?
可以说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但我并不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互联网只是为放大人性中的某些方面提供了方便和机会。在19世纪的机器时代,也有人担忧机器会改变世界,改变人。世界是改变了,但人还是人。人性是在上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人的基因中一代代传下来。机器时代或互联网时代不过百十来年,根本来不及从基因上改变人性。今天疫情中所有发生的事情,恐惧、焦虑、道德崩溃、阴谋论、假消息、逐巫、好了伤疤忘了疼等等,有哪一样是在古代的瘟疫时期找不到的呢?这些都不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而不过是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已。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描绘的雅典瘟疫发生在战争发生的第二年。历史记载上还从来沒有哪个地方的瘟疫像雅典的瘟疫一样厉害,或者伤害这么多人。起初,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病,向神庙祈祷、询问神讖等等办法也都无用处。最后,人们完全为病痛所困倒,所以他们也不再求诸占卜了。他们因无助而陷入了恐慌和绝望。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对瘟疫的描绘是令人惊骇的:“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征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闷,接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没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人倒在地上,死了。
更可怕是人性的崩溃和放弃了信仰,雅典人一下子从人变成了兽类。希腊人相信,宇宙间只有三种存在,都是以对待死者的方式来区分的。第一种是神,神是不死的,无需安葬。第二种是人,人死而必葬。第三种是兽类,兽类死而不葬。雅典的死人一天天多起来,活人变得像兽类一样。临死的人没有亲人陪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活着的人不再安葬死者,尸体就被丢弃在空地上,连鸟兽都不敢接近这些尸体。修昔底德写道:“有许多死者的尸体躺在地上,没有埋葬,吃人肉的鸟兽不是不跑近尸体,就是,如果尝了尸体的肉的话,后来就因此而死亡。……这给狗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因为它是和人住在一起的”。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在记录1665年伦敦大瘟疫的《瘟疫年纪事》一书里也有可怕的描述,细节不同,但人性的崩溃和信仰的丧失却是相似的。
更可怕是人性的崩溃和放弃了信仰,雅典人一下子从人变成了兽类。希腊人相信,宇宙间只有三种存在,都是以对待死者的方式来区分的。第一种是神,神是不死的,无需安葬。第二种是人,人死而必葬。第三种是兽类,兽类死而不葬。雅典的死人一天天多起来,活人变得像兽类一样。临死的人没有亲人陪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活着的人不再安葬死者,尸体就被丢弃在空地上,连鸟兽都不敢接近这些尸体。修昔底德写道:“有许多死者的尸体躺在地上,没有埋葬,吃人肉的鸟兽不是不跑近尸体,就是,如果尝了尸体的肉的话,后来就因此而死亡。……这给狗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因为它是和人住在一起的”。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在记录1665年伦敦大瘟疫的《瘟疫年纪事》一书里也有可怕的描述,细节不同,但人性的崩溃和信仰的丧失却是相似的。
绘画中的1665年伦敦街头
互联网时代用不着等待某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来为我们记录灾难。灾难发生的时候,平常的普通人就能把他们的经验、体会和生活中的痛苦遭遇和酸甜苦辣通过网络告诉他人,传播的信息有的可能只是在网上存在几个小时,有的人也会因此遭到谩骂、攻击或其他的麻烦。但人绝不会断了上网的念头,也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不管发生什么,有一个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那就是,网络是人类思维和言论的网络。
面对疫情,您认为知识分子在此时应该扮演一种什么角色、起到何种作用?疫情中,很多知识分子都以日记的方式进行记录,当然也有很多普通人也在写这样的日记。您觉得这样的文字有何意义,两种日记在价值上又是否有所不同?而像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日记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您对此有是否有自己的看法?
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扮演理性观察者和批评者的角色。如果他有能力、有时间和精力,不妨也可以做一点像修昔底德和笛福那样的纪事工作,至于采取什么形式,最好是灵活的,有创造性的。就拿笛福来说,他的《瘟疫年纪事》经常受到“不真实”或是“虚构”的指责。伦敦“大瘟疫”在1665年爆发的时候,笛福还只是一个小孩。那本在他成年之后撰写的书是将资料研究、个人回忆、想象以及可能由一个当时一直生活在伦敦的叔叔所讲的故事集于一体的混合著作。不过,它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份经典记录,当中写下的场面和观察,会令2020年的读者产生真切的共鸣。而当中关于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描写,令当下的我们感觉尤为熟悉。
这个被称为COVID-19的疫情如果发生在社交媒体革命之前,人们的体会反而会显得更加真实。1722年,笛福写下《瘟疫年纪事》的时候,提醒过他的读者,在他的童年时代,报纸几乎是不存在的。
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日记因她田园诗般的隔离生活描述,引发了不少法国同行作家们的不满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的10位青年男女也是为了逃避瘟疫到乡下去享受他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瘟疫只是这本书叙述框架的一部分,一个背景,没有人会把《十日谈》与对瘟疫的体验特别联系起来。斯利玛尼的避疫日记受到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把她比作法国大革命前遭法国人痛恨和鄙视的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称她描绘的那种生活是格林童话里的虚构故事。在人类的灾难面前,有良知和同情心的人们会对艺术和写作设立某种起码的道德伦理标准,一个作家不应该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更不应该拿别人的不幸来衬托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比斯利玛尼更棒的女作家。

面对疫情,您认为知识分子在此时应该扮演一种什么角色、起到何种作用?疫情中,很多知识分子都以日记的方式进行记录,当然也有很多普通人也在写这样的日记。您觉得这样的文字有何意义,两种日记在价值上又是否有所不同?而像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日记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您对此有是否有自己的看法?
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扮演理性观察者和批评者的角色。如果他有能力、有时间和精力,不妨也可以做一点像修昔底德和笛福那样的纪事工作,至于采取什么形式,最好是灵活的,有创造性的。就拿笛福来说,他的《瘟疫年纪事》经常受到“不真实”或是“虚构”的指责。伦敦“大瘟疫”在1665年爆发的时候,笛福还只是一个小孩。那本在他成年之后撰写的书是将资料研究、个人回忆、想象以及可能由一个当时一直生活在伦敦的叔叔所讲的故事集于一体的混合著作。不过,它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份经典记录,当中写下的场面和观察,会令2020年的读者产生真切的共鸣。而当中关于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描写,令当下的我们感觉尤为熟悉。
这个被称为COVID-19的疫情如果发生在社交媒体革命之前,人们的体会反而会显得更加真实。1722年,笛福写下《瘟疫年纪事》的时候,提醒过他的读者,在他的童年时代,报纸几乎是不存在的。
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日记因她田园诗般的隔离生活描述,引发了不少法国同行作家们的不满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的10位青年男女也是为了逃避瘟疫到乡下去享受他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瘟疫只是这本书叙述框架的一部分,一个背景,没有人会把《十日谈》与对瘟疫的体验特别联系起来。斯利玛尼的避疫日记受到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把她比作法国大革命前遭法国人痛恨和鄙视的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称她描绘的那种生活是格林童话里的虚构故事。在人类的灾难面前,有良知和同情心的人们会对艺术和写作设立某种起码的道德伦理标准,一个作家不应该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更不应该拿别人的不幸来衬托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比斯利玛尼更棒的女作家。
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
您写过《明亮的对话》来讨论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言说与沟通。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公共氛围并不容易存在,甚至某种程度上是稀缺的。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
根本的原因在于是否说真话。说理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让人开口说话,第二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理,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存在,说理就是一句空话。
19世纪伟大的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写过一个题为《人民公敌》的剧,剧里有一个富有医学专业精神的人——斯多克芒。斯多克芒有一个担任市长的哥哥,他们共同负责一个小镇上发展温泉浴场的计划。小镇投资了一笔为数甚大的资金支持发展,而镇民们也巴望具有医疗价值的温泉浴场可以带来旅客,令小镇大大兴旺。
因此,浴场对小镇声誉便有了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当温泉浴场开始渐露曙光时,斯多克芒发现市内的制革厂在污染温泉的水源,而且引致旅客患上严重的疾病。他认为这个重要发现是自己最大的成就,立即将一份详细的报告发送给市长,告诉他环境污染的严重隐患。用报告的方式与市长沟通,这是说理的方式。
指望浴场会带来财富的市民们拒绝接受斯多克芒的说法,甚至之前支持他的朋友和盟友,现在也反过来百般指责斯多克芒,说他是为了自己出风头。他被市民奚落和谩骂,甚至被斥责为疯子,还有人朝他的办公室丢石块。
最后,当地的居民表决宣布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他就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的真话,而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坏人”。

根本的原因在于是否说真话。说理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让人开口说话,第二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理,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存在,说理就是一句空话。
19世纪伟大的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写过一个题为《人民公敌》的剧,剧里有一个富有医学专业精神的人——斯多克芒。斯多克芒有一个担任市长的哥哥,他们共同负责一个小镇上发展温泉浴场的计划。小镇投资了一笔为数甚大的资金支持发展,而镇民们也巴望具有医疗价值的温泉浴场可以带来旅客,令小镇大大兴旺。
因此,浴场对小镇声誉便有了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当温泉浴场开始渐露曙光时,斯多克芒发现市内的制革厂在污染温泉的水源,而且引致旅客患上严重的疾病。他认为这个重要发现是自己最大的成就,立即将一份详细的报告发送给市长,告诉他环境污染的严重隐患。用报告的方式与市长沟通,这是说理的方式。
指望浴场会带来财富的市民们拒绝接受斯多克芒的说法,甚至之前支持他的朋友和盟友,现在也反过来百般指责斯多克芒,说他是为了自己出风头。他被市民奚落和谩骂,甚至被斥责为疯子,还有人朝他的办公室丢石块。
最后,当地的居民表决宣布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他就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的真话,而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坏人”。
北京人艺版《人民公敌》剧照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有待创造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言说与沟通的条件。现在一些所谓的争论,其实只是自说自话,只是在强化说话者自己的立场,而根本无法说服对方。这尤其表现在互联网时代的回音室效应和部落思维方式上。
由于信息流通的差异,国外讨论的一些问题,也与国内的不在一个层次上。例如,在美国就有这样的情况,州政府要求居民在家隔离,有的民众却上街抗议,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在疫情中找到了对民众的政治优势,因此无视他们的生计需要。由此产生的争论和说理需要有一个理性、自由的讨论环境,不然就会变成屁股决定脑袋的无谓争论,让说真话的人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二战后出现的全球化的一些成果,好像在这次的疫情中被消解了,开放的边界关闭了,合作应对的情况也不明显,甚至出现西方国家之间拦截口罩的现象,包括疫情对供应、运输的阻断显露出贸易全球化的劣势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困境。因此不少人对全球化的未来更为悲观。您怎么看待全球化的未来?
二战后出现的是世界性的人道主义共识,它的标志是联合国1948年底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那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全球化”,今天的全球化是一种经济和贸易功利主义的全球化,它的指挥棒是经济利益,不是共同的人道价值。破坏和颠覆二战后世界人道主义的正是这种唯利是图的所谓全球化。
疫情把人的生命、人的尊严问题重新放在了全世界人们的面前,乘人之危的经济行为已经越来越被人唾弃。这样的全球化被消解,被阻断未必是一件坏事,也不需要为之惋惜,或感到悲观。
我在《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一书里提出,全球化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建立在一个“新全球伦理秩序”上,以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冲突来看,这样的全球化化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渺茫的幻想。
人类是从无数灾难中一路走过来的,有些灾难在带给人苦难过后,也成为了某种进步的基础或契机。您觉得,这次的疫情会在苦难之外带给我们什么呢?
虽然我相信,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次疫情肯定会被当作一次空前的灾难记载在历史中,但我不知道它会给我们这个特定的群体带来什么后果。灾难是否成为进步的契机不取决于灾难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
由于信息流通的差异,国外讨论的一些问题,也与国内的不在一个层次上。例如,在美国就有这样的情况,州政府要求居民在家隔离,有的民众却上街抗议,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在疫情中找到了对民众的政治优势,因此无视他们的生计需要。由此产生的争论和说理需要有一个理性、自由的讨论环境,不然就会变成屁股决定脑袋的无谓争论,让说真话的人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二战后出现的全球化的一些成果,好像在这次的疫情中被消解了,开放的边界关闭了,合作应对的情况也不明显,甚至出现西方国家之间拦截口罩的现象,包括疫情对供应、运输的阻断显露出贸易全球化的劣势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困境。因此不少人对全球化的未来更为悲观。您怎么看待全球化的未来?
二战后出现的是世界性的人道主义共识,它的标志是联合国1948年底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那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全球化”,今天的全球化是一种经济和贸易功利主义的全球化,它的指挥棒是经济利益,不是共同的人道价值。破坏和颠覆二战后世界人道主义的正是这种唯利是图的所谓全球化。
疫情把人的生命、人的尊严问题重新放在了全世界人们的面前,乘人之危的经济行为已经越来越被人唾弃。这样的全球化被消解,被阻断未必是一件坏事,也不需要为之惋惜,或感到悲观。
我在《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一书里提出,全球化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建立在一个“新全球伦理秩序”上,以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冲突来看,这样的全球化化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渺茫的幻想。
人类是从无数灾难中一路走过来的,有些灾难在带给人苦难过后,也成为了某种进步的基础或契机。您觉得,这次的疫情会在苦难之外带给我们什么呢?
虽然我相信,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次疫情肯定会被当作一次空前的灾难记载在历史中,但我不知道它会给我们这个特定的群体带来什么后果。灾难是否成为进步的契机不取决于灾难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