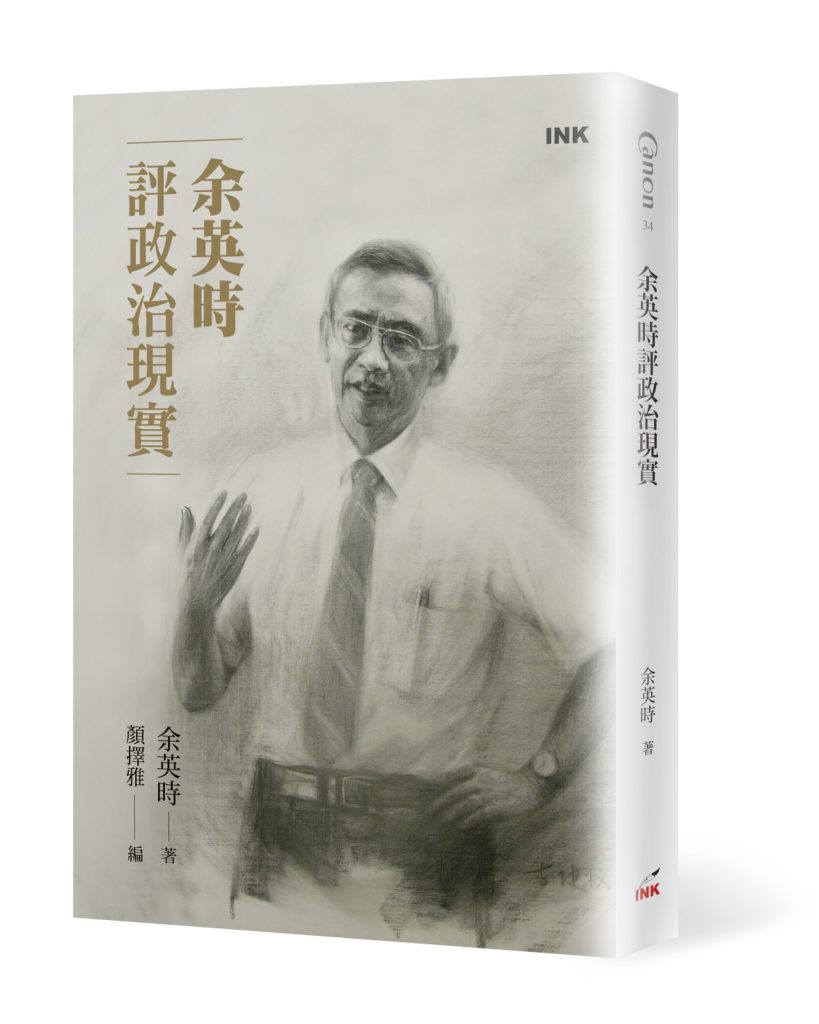
不打算全面性的評論《余英時評政治現實》,而是談一個概念,且先從一則往事開始。
確切時間已記不得,但大概是96年台海導彈危機之前,「時報文教基金會」邀請余英時先生至報社八樓辦了場演講,講題我也忘了,大意就是評析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共動向。眾人皆知余先生一生反共,他罵起中共是絕不留情,在該次演講中,余先生痛斥中國共產黨是「滿洲黨」,我祇見站在我身旁不遠的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先生,雙手交叉於胸前,頭抬得高高,他對余英時的不以為然溢於言表。
我倒不認為余老闆純粹是媚共──雖然90年代以後,整個中時報系對中共政權的批判少之又少,透露出余老闆想西進的野望,阻卻了民主優位的奠基。我思考的是一整個四九年後移民來台的前後世代,到了90年代本土意識崛起後,他們之中不少人陷入返祖危機。余老闆如此,自由憲政捍衛者胡佛亦然,再年輕一些的所謂開明學者、文化知識人也逃不掉此一緊箍束縛。這種返祖現象於今猶烈,何以致之?除了傳統民族主義的召喚,也該有個更鮮明的詮解才是。
「羡憎交織」是大一統人士的共病
思緒再讓我回到1996年台海危機前後的言論天地。余英時先生當時先後给予《中國時報》兩篇長文極力解析中共政權的思邪走偏。先是〈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給了「時論廣場」,兩個月後局勢平撫,他給了「人間副刊」一篇更長的〈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兩篇都深刻剖析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而其中貫以一個極具意義的概念──「羡憎交織」(ressentiment),由於後文係由我經手編輯,特別有感、殊值一談。
按余英時先生的說法,「羡憎交織」係源於尼采的思想概念,意指企羡和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而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地表達出來。當代社會學家格林菲德(Liah Greenfeld)借用來研究當代民族主義,認為上述那種心理是「落後民族對於先進民族的典型反應。落後民族自覺它的地位應該和先進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但在現實中卻高下懸殊,因此一方面效法先進而好像永遠追不上。另一方面則滋長著憎恨先進的情緒而想打倒它。」
在余先生筆下,俄、德是極好的實例。而「中國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百餘年來卻受盡各『先進國家』的欺壓。…『羡憎交織』的民族情緒使不少中國人期待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式的強國,在國際上耀武揚威,為自己吐一口氣,這是『羡』的情緒的表現。他們更願意看見中國用武力打敗西方強國。所以中共參加韓戰,和美國展然打得相持不下,他們引以為驕傲的,並以為中國的強大已得到了證明。這是『憎』的發洩。」看看去年(2021)中國拍製《長津湖》的用意,完全符合余先生的指涉。
這種「羡憎交織」心理和一般亞、拉、非第三世界標榜的反殖反帝不一樣,因為後者祇有平等、安居的渴望,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望雄心。祇有像中國、俄羅斯、德國、土耳其、伊朗這些曾有過帝國榮光的今之「哀怨國度」才可能醞釀出嗆辣夠勁的「羡憎交織」。
當余英時先生在90年代中期提出這種解析,確實激怒了渴慕富國強兵、重振中華的所有大一統人士,當時的新黨紅人朱高正就讓其助理林深靖攜其手稿至「人間副刊」辦公室試圖踢館,遭「人間副刊」見拒後,就以〈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為題轉登於《歷史》月刊。朱文大意就是余先生觀點盡是摭拾西方、美化台獨、醜詆中國。我也相信余先生這兩篇宏文的確觸怒了中時余老闆,據說他就此下了道指令──爾今爾後不再邀余英時文章。以致直到2002年4月余老闆過世,我們方才邀余英時寫悼文。
也許,在90年代中期中共政權尚屬韜光養晦,其軍經實力完全無法與美國相頡頏的條件下,「羡憎交織」的說法會予人過苛感受,且欠缺各種後設的排比。但余先生談的是本質,是綜觀中共歷史與剖解同情中共者心態所得出的病症說明。結果20年後看看如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什麼戰狼外交、小粉紅肆虐、一帶一路、強控回藏、鎮壓香港、兵陳南海、緊束台灣……,俱屬「羡憎交織」的八方箭射。再次回顧余先生當日的讜論,祇能驚歎是先知之言。
學識之外,更得保持清醒心靈
余先生作為鴻儒,論史談經大概沒多少人有意見;但由於他堅定反共,所以他的現實論政文章就會招惹太多褒貶,且隨著「中國崛起」的滔天巨浪,余先生在被貼上「反華仇華勢力急先鋒」、「充當台灣當局領導人的教頭」之餘,恐怕更多已附和中共政權的人士會譏他「反共過激」、「反共無用論」。但這些附共成員似乎遺忘了30年代西方不少大知識菁英、文化雅士齊心歌誦獨裁、棄置民主的往事,以致今日一步步牢貼於「羡憎交織」的牌位,逐次走向為專制服務的永劫回歸而不覺。
「羡憎交織」結合中共「黨天下」思惟,對內專制、對外張揚,這些都是余先生論述中共政權與領導人的根本題旨。由於直指核心,使得余先生的觀點如滾石般鮮活,一點也沒過激、過時問題。更重要的是,余先生考察中國歷史得證,知識人就是在抵抗與馴化之間作選擇,余先生以其言教身教告訴了世人,祇要無欲、頭腦清明,站在抵抗專制一方是絕對可能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