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他的离去,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感到失去了一位导师、楷模和朋友。为了纪念这位精神巨人,我将2006年1月和3月搜集到的《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翻译和出版经过的有关访问整理发表,既是对索尔仁尼琴的追念,也是对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年代的缅怀。
我与《古拉格群岛》的中文译者之一田大畏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早年开始学习俄文,长期从事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翻译过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多次出访苏联,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2006年1月,为搜集中国“解冻史”素材,并请教苏联五十年代“解冻”与中国八十年代“解冻”的关系,我访问了田大畏先生。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1970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它在自己的祖国却没有获准出版。但据说,这本书的缩微胶片被带到了出去,1973年在法国出版。您是该书的译者,您是什么时候,怎么会想到要翻译这本书的?
田大畏(以下简称“田”): 翻译《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主动找人翻译的。后来于浩成说是他的想法。我和他是华北大学的同学,而且是一起出来工作的。他那时候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他们开始是想从英文翻译,找到北图。但他们找的那位懂英文的同志建议直接从俄文翻译,于是就找到我。
 |
| From 人物 |
索尔仁尼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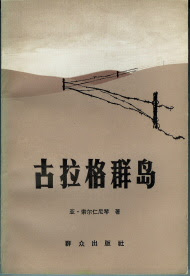 |
| From 人物 |
中译本《古拉格群岛》初版
陈:《古拉格群岛》的中文版是1982年出版的。距它的俄文初版只有9年,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刚刚开始不久,全书53万余字,你们也译得够快的……
田:实际上这个工作是1979年完成的。我和一个好友(陈汉章)共同翻译了上、中册,另一个同志(钱诚)翻译了下册。交稿后一度被搁置。后来胡耀邦批准每年出版一批西方社会科学的书,《古拉格群岛》被列入名单。到1982年才出来。作为“甲类”内部书发行,就是要登记购买者。其实后来也没控制住。作协四大,也就是被认为最“自由化”的那一次,群众出版社的人蹬了个三轮到会场卖,就没什么限制了。结果一版再版……
陈: 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西方文化逐步取代苏联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但在“解冻”的开始,还有一个以苏联五十年代“解冻”文学为前 导的时期。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模仿苏联“解冻”文学的作品。您能否谈谈当时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人们期望从中汲取的思想资源?
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研究和翻译苏联文学的工作开始活跃,成立了苏联文学研究会。对苏联文学,重新产生了好感。在我国文革浩劫之后,更感到人道主义之可贵。但有人(后来成为很受重用的人)反对,发生争论。1980年在哈尔滨开会,陈冰夷讲话肯定赫鲁晓夫的贡献,与会者对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是一致称赞的,哈尔滨文学刊物(好像叫“文艺百花”?)大胆登了详细报道,结果被查封。
在 这以前译载苏联当代作品还有顾忌,如王金陵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时,加了一个批判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前言,说它宣扬资产阶 级人性论,宣扬战争残酷,褒扬苏修忠实奴才等等。因此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译载苏联作品是搞“曲线的反苏主义”。其实他们是被自己盲目的反华主 义蒙蔽,看不到在中国出现的新的风向,不懂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的苦衷……
陈: 您说的这个现象很有趣。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很容易把中国想象成“铁板一块”。如果这样,中国“解冻”时代的思想洪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实际上, 中国不仅有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而且在中苏交恶最严峻的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表达仍然很顽强。有一篇叫做《关连长》的短篇小说,写于1949年11月。 它讲述的是解放上海时,一位连长率领战士摧毁国军据点的故事。不巧这个据点是一所学校,房间里挤满了孩子。敌人想利用这些孩子作掩护,关连长得知这一情况 后,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以 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
 |
| From 人物 |
中国电影博物馆中的《关连长》剧照
1957年, 巴人、钱谷融、王淑明等人还在文艺理论界掀起过一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巴人呼吁文学艺术恢复人道主义传统。他指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些呼声虽然遭到了批判,但它只不过是被压到了地下一遇机会,它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冒出来。以后,又出现了象《北国江 南》、《早春二月》这类人道主义题材的作品。最有趣的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人道主义论战的两位旗帜性人物——周扬和王若水。1963年 正式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囗号,王若水是被“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 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曾联合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刘少奇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个任务落到了日后另一 位“起义”者——周扬的肩上。我想,正是这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收集古今中外的“人道主义”资料,并进行比较和研究,为日后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行这类批判,1966年以前,中共出版了大约1,041本 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即俗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内部读物。其内容大多是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中“异端”的作品。文革的“破四旧”活动,使大量过去只限 于高干阅读的书籍流散民间,成了知识青年思想解放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不见于正式报刊的社会现象,外界无从了解,所以难免产生误会。
田: 苏联的解冻,除了总的形势,我觉得还有几方面的资源,一是前面说过的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已渗入了普通俄国人的灵魂,始终未能改变。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和苏联朋友谈反对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他们(即使是非常友好的朋友)是不能理解的,不能接受的。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俄国领土大部在亚洲,但俄罗 斯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欧洲的”与“文明的”是同义语,而“亚洲的”代表落后、愚昧与野蛮,如他们往往说“亚洲式的残忍”,“东方式的 专制”。西方古典文化从来受崇敬,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包括美国)现代文化涌入苏联势如潮水。三是被压制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的“复活”。小说家、诗人帕 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城》),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皮利尼亚克,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大量 的文学、戏剧、电影方面大师级的人物的恢复名誉,成为受人热爱的新的经典,我读过和翻译过其中人的几部作品,感到俄罗斯的文学长河是由他们延续的。在最严 酷的年代里,这条长河变成了潜流,但从未中断。四是长期流寓国外的俄侨作家(作品)的“回归”。他们的水平和影响远非离开中国大陆的文艺家们所能比……
陈: 看来,一方面是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方面是中共“以俄为师”的传统,一方面是中苏弊症的同构性,这三重因素,造就了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 必然要以苏联“解冻”时期的风格作为楷模……我的朋友中,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麦德维杰夫”自任者,不乏其人,可见其示范效应。而您是这个过 程最早的铺路者,却很低调……
陈:索尔仁尼琴逝世了,您对于他,对于他的《古拉格群岛》有什么评价?
田: 索尔仁尼琴的去世,使我忽然想起来鲁迅的《无题》中的两句话:“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他像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在似乎无望的 绝境中思考着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的、历史的、人类的大问题,并且毫无顾忌地表述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坚守他的良知、尊严和责任感,即使被本国驱逐而多年流 亡国外,也绝不投人所好,这也是某些中国政治流亡者所不及的。索尔仁尼琴暗中写作《古拉格群岛》时,苏联是一个“无声”的社会,或者是被“主旋律”统治的 社会,他的作品推动了苏联社会从“无声”到“有声”的转变,从“单声部”到“多声部”的转变。 曾十分流行的“公开性”(英文音译为glasnost)这个词,俄文字根就是“声音”,转意为“发言”、“表决”、“宣告”、“公开”。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称为无声处的惊雷,也许不为过,仅此一点,他对俄国社会进步的贡献就是很大的了。
2006年3月,经田先生介绍,我就同一个问题访问了归国不久的于浩成先生。
于先生192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1942年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7岁入党,建国后,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八十年代初期任公安部所属群众出版社社长。
陈:于先生,您是怎么想起要翻译出版《古拉格群岛》的?
于浩成(以下简称“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给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研究苏联问题……
陈:当时是您个人研究还是工作条件许可?
于:合法地研究。文革前,党内就有斯大林问题研讨会,各个部都有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当时,除了公开出书外,内部也在搞研究。有一本内部刊物,叫《政情研究》。文革结束前,我们就开始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文革结束后才出书。
陈:文革末期?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能被批准吗?
于:当时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胡乔木批示:“编号发行”。
陈:“编号发行“是什么意思?
于:就是每个买书的人,要登记姓名、单位、住址。
陈:听说在作协“四大”的时候,这本书引起了轰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于:我是作协“四大”的特邀代表。我们出版社把书拉到大会,作协会员可以凭证购买,立即抢购一空……巴金当时在上海没有来,给我们写信要,结果张欣辛回去送给了他。巴老还来信表示感谢。
陈:七十年代末期,出了一批“灰皮书”,像《新阶级》这些,对一代青年的启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能不能谈谈当时出版这批书的背景?
于:群众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大字本的《新阶级》,是彭真让搞的。我写的序言。后来,领导说我的序言不能用。这篇文章后来在张显扬他们出的一本刊物上发表了。
陈:当时中共党内的“苏联问题研究”是一种什么状况?
于: 关于斯大林问题研究,我们能看到各国党的讲话。我说,铁托的讲话讲得最好,问题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当时是党内一批,社会上民 主墙一批。我当时讲,邓小平说:毛泽东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法制,在英、美、法等法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按自己的认识去 做,所以才犯了文革的错误。我说,由此看出,邓小平并不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分权制衡”的原则。后来邓小平出来澄清,明确反对“三权鼎立”……
陈:是不是因为邓看了您的讲话以后,才发生有针对性的澄清的?
于:那倒不一定。因为后来引用他的这段话的人很多了……
陈:也可能这些引用是从您开始的,因为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法治问题……
于:那倒有可能。我最早撰文区别“法制”和“法治”的概念。毛泽东曾经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
陈:是吗?还真讲过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于:这句话没有收入毛的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语录,《人民日报》当年有传达,后来我看到有一个材料,说文革中广州有个小报也刊出了,知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毛大概是1959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这么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陈:人道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块基石。现在有人说毛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何好。但没有这两块基石,就不在人类文明——“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大道上。

From 人物
2008年2月,作者(右)与田大畏先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