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聯經之間從一開始便遠遠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家的契約關係。我每次在聯經出版一本書,都覺得是一次友情的交流。」
余英時先生於1971年夏天初訪台北和日本。這次行程給他帶來了一個很意外的感觸,他發現他的英文著作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1973-75年,他正好回到香港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於是決定用中文著述,這個決定也讓余先生開始與台灣產生了一生的密切關聯。這一年,余先生來台時又經友人介紹,認識了後來的聯經發行人劉國瑞,兩人開始建立長期的友誼,也為余先生與聯經的關係鋪下了基礎。
一、《歷史與思想》,1976
我曾在「燃燒的七十年代:《歷史與思想》二十年」(聯合報,1996.7.1.)一文中提到,1975年是台灣思想發展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林毓生先生首度返台任教,在五月份的《中外文學》發表了一篇長文:「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點燃了沉悶氣氛下青年學生重探狂飆年代的興趣。隔年(1976)一月,余英時先生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九卷一期發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接著《聯合報》副刊陸續刊載「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三篇文章,為當時爭論不休的「一人專制」問題提出了非常有説服力的解釋,引起了許多辯論。特別是明清思想轉折由「尊德性」到「道問學」的「內在理路」說,彰顯思想本身有其內在生命的觀點,更是為知識界帶來極大的震撼,因為當時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思想的變動來自外在因素的影響。
1976年9月,余先生將上述文章及其他論文結集為《歷史與思想》,由聯經出版,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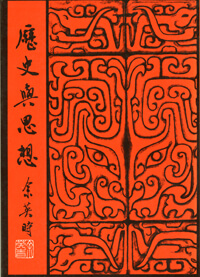
《歷史與思想》自出版後廣受閱讀,幾乎以一年一刷的速度進行,至今已四十五年,就台灣的學術著作而言,是非常少見的例子。2014年,在出版三十八年後,聯經又重新排印,余先生為此又作一「新版序」,提到「這是我個人出版史上一件最值得珍惜的大事」,這本書「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序中並回顧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所引起的爭辯,以及這本書在他個人學術生命中所具有的極不尋常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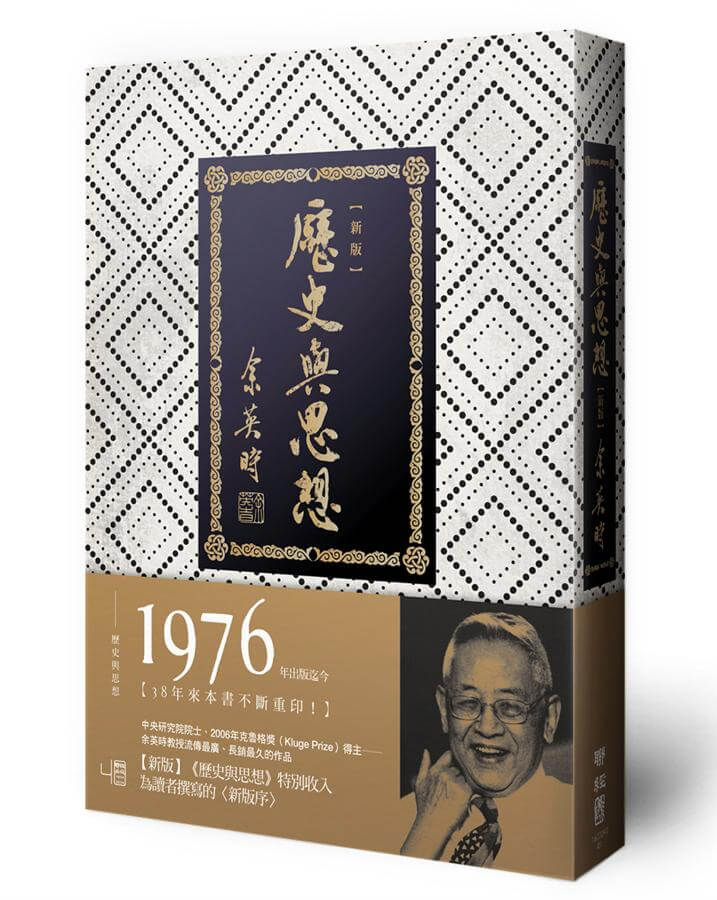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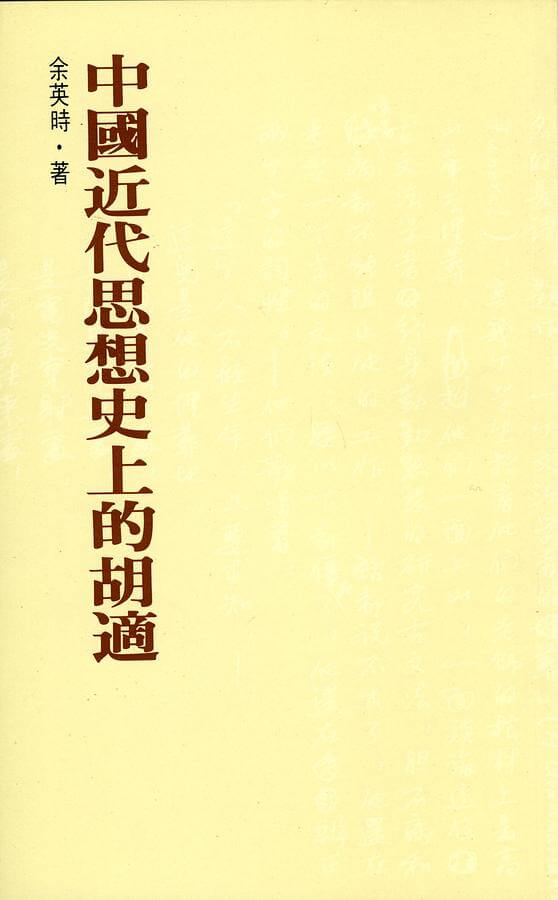
三、《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2004
2004年初,聯經準備要出版四百萬字的《胡適日記全集》,因而再度邀請余先生撰寫一篇序文,余先生說:「聯經出版公司毅然決定出版這樣一部龐大的日記,其原動力只能來自一種純淨的文化理想。⋯我在『義不容辭』的直感下一口答應了。」他並說,要「把《胡適日記全集》的史料價值充分而又系統地呈現出來。」經由《日記全集》的引導,余先生逐漸進入了胡適的世界,「反覆考慮之後,最後決定根據《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把胡適的一生分成幾個階段,並分別點出其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於是一篇序文就發展成了將近九萬字的《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的專書。
2004.4.15,余先生的信上這麼說:
載爵兄:
謝天謝地,總算寫完了最後一個字。
此文寫得如此長,實非始料所及。我心裏十分焦急,真怕誤了你們的作業。但我又不能潦草結束,有首無尾。只好拼老命日夜趕工,也不知究竟連累你們到什麼程度,現在後悔已不及矣。一個月寫了八、九萬字,此亦平生第一次的經驗,以後再不敢嘗試了。
看到「拼老命日夜趕工」,「以後再不敢嘗試了」,我真是既感謝又抱歉。然而,這本由短序變為專書的長文(後以此長文為主,加上其他有關胡適的文章,輯為《重尋胡適歷程》出版),卻利用了新史料為胡適勾勒了一個新的生命歷程。例如,挖掘出與 Roberta Lowitz 的一段情緣,澄清了胡適生命史上的兩個疑點:博士學位問題和哲學造詣問題。余先生引用日記資料,說明胡適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又在日記中發現1923年羅素(Bertrand Russell)為美國著名雜誌 The Nation 寫了《先秦名學史》的書評,說明胡適的西方哲學至少是合格的。至於引起最多爭論的博士學位問題,余先生除了在書中有所引證陳述之外,半年後又撰一文:「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引用胡適的日記、書信和英文著作做為證據,為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作了最明確的澄清,余先生說:「八十五年來的一件疑案終於完全消解,再也沒有爭論的餘地了。」
他在2004.11.17的信中這麼說:
載爵兄:
近寫「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一文已成,一再斟酌,終於定稿。‧‧‧我自覺此文發掘了胡先生生命史上重要的一頁,為從來所不知,不僅澈底澄清「學位」問題而已。我的胡適研究至此已終結了。
如信中所言,寫完這本由序轉為的書之後,余先生的胡適研究就告一段落。
除此之外,還要提到一件別具意義的事。余先生2004.4.21的信特別交代編排時務必:
把「知識分子」改為「知識人」,我越來越不喜歡把「人」看成某種「分子」,所以再不用「知識分子」了。請注意。
我們都可以注意到,余先生的確在2004年之後,不論行文或訪談,就以「知識人」取代了「知識分子」。

四、《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006
在一個月之內,「拼老命」把原來的短序寫成《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的專書之後,余先生說:「以後再不敢嘗試了」。
2006年,聯經又準備出版六百萬字的《顧頡剛日記》。這是顧頡剛除1913年及1919年的片段記載外,自1921年起,歷經六十年未曾中斷的日記,不僅是顧頡剛個人完整的生命史記錄,更是一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寶貴材料。基於這部日記的重要性,聯經再度邀請余先生撰序,而且說明是短序。余先生再度義不容辭的答應。沒想到歷史再度重演,原來的短序又發展成為十萬字的專書:《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這是余先生第三次為聯經的大套文獻由寫序變為寫出一本專書。
2006.11.19的信說:
載爵吾兄鑒:
顧《日記》序總算寫畢,勉可交卷。近一兩月事忙,不能專力於此,屢作屢輟。初只欲寫一簡要序言,提綱挈領,以為讀《日記》者之一助。但因材料太多,頭緒紛繁,愈整理則頭緒愈多,終至辭長不殺,真非得已。全稿完成後,回顧前面一、二節,又嫌過簡,結構嫌散,因此復改寫多頁。若有時間,從容再刪定一次,當比目前之稿為好,但實已不可能矣。此序內容甚新,因《日記》為初刊材料,我對於顧本人,從未暸解到如此深度,新史料才能成新史學也。
「辭長不殺,真非得已」這八個字正足以說明由「義不容辭」到「下筆不能自休」的寫作過程。這篇序文與《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不同,讀胡適日記時,余先生採取藉日記的材料解答胡適一生各個階段的若干疑點的寫作角度,到了讀顧頡剛日記,則改為通過日記來窺測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余先生發現顧頡剛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生命型態比較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更意外的發現是,顧頡剛「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讀來極為動人。」這篇序文,就是深入顧頡剛的內心世界來瞭解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堪稱是首度揭露顧頡剛真實人生的第一部作品。
余先生在交出稿件後一星期(2006.11.28.),寫了一封信給劉國瑞先生,談及本書稿酬的處理辦法:
國瑞吾兄道鑒:
近日屢得在電話中承教,至以為慰。茲有一點想法,經深思熟慮而得之,亦得內人淑平熱烈贊同,向兄鄭重提出,務乞俯允,並助弟完成一種誠摯之心願。此次為《顧頡剛日記》所撰序言,及另印單行本,弟擬獻於王惕吾老在天之靈,不受稿酬及單行本版稅,此書版權全部讓給聯經公司,即以此為憑。如聯經另有法律合同,需弟簽字,請寄版權轉讓(贈送)文件,弟必立即簽字後寄上,以完備法律手續。弟此意極誠極堅,務請兄垂鑒。無論如何,弟決不收任何酬報,如聯經寄來,弟亦只可退回,為此往復,大可不必。弟之微意,請兄體諒。此即昔人所謂「秀才人情」,殊不足道,然在弟則等於向惕老墳前燒一柱香也。
余先生在信中表達不接受任何報酬的意願,其背景我想是感念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對學人與文化事業的長期支持,包括《錢賓四先生全集》的出版(共五十四冊,1994-1998)等等。另外則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王惕吾先生對受到影響的學人、學生提供資助,並委由余先生處理。(請見丁學良:「非常之時追憶非常之人」)
儘管余先生表達了這樣的意願,但聯經還是覺得必須支付稿酬,以答謝余先生的辛勞。合約寄出後馬上收到余先生的回簽,但是在合約上加上了下面的聲明:
本書所有稿酬及版稅一律轉贈「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余英時親筆
2006.12.18於普林斯頓
作為「士」、「君子」、「知識人」,余先生的高風亮節在這裡完全顯現出來。
2014年5月4日是聯經創立四十週年,余先生撰寫「感受與追憶」一文(刊於《聯合報》副刊,2014.5.1.)期勉聯經,文中也提到了這兩次由序成書的經驗:
繼國瑞先生主持聯經的是林載爵兄,我和聯經的友誼關係也通過載爵兄而延續了下來。他和我是歷史學的同行,思想上的溝通也一向順暢。事實上,自從他在1987年擔任聯經的總編輯以來,我們之間的往復已日趨頻繁。關於我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2001)和八十歲生日(2010)的兩部論文集,篇幅既大,又不可能暢銷。載爵兄竟一本聯經傳統,毅然出版,使我十分不安。我只有將這種深厚情誼永藏胸中。
但我和載爵兄之間,作為作者與編者,卻有兩度最愉快的合作。載爵兄在出版《胡適日記全集》和《顧頡剛日記》之前都先後邀我寫「序」——延續我為胡適《年譜》寫序的傳統。他並沒有要我寫長序,然而我為了不負他的信託,兩序都是下筆不能自休。這是限時交卷的工作,不容我有所延誤,因此我夜以繼日,寫得非常緊張,也非常暢酣,是我寫作史上兩次最難忘的經歷。現在寫出來作為我們之間友誼的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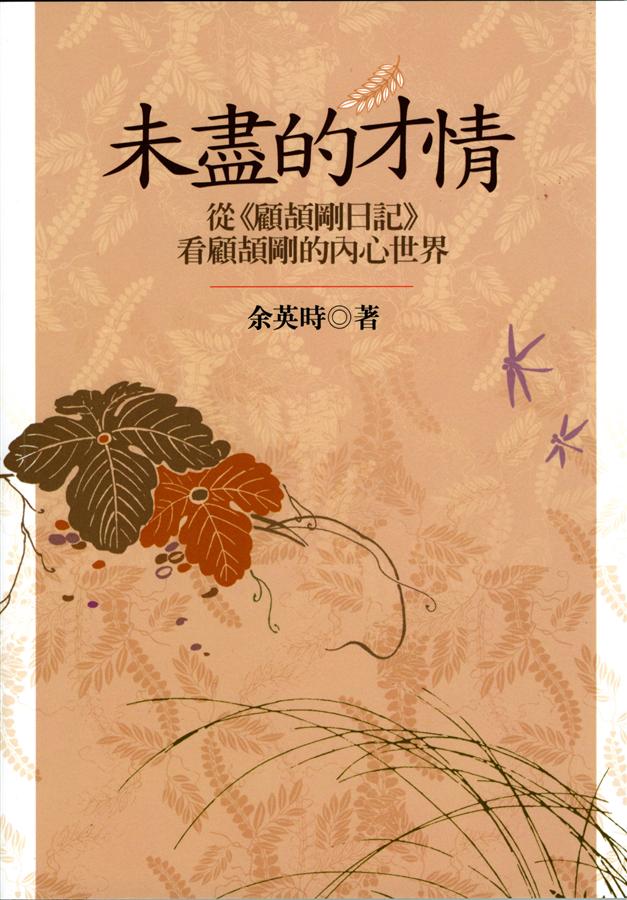
五、友情的交流
余先生對學人、對聯經的照顧,還包括會推薦優秀的著作給聯經。
2011.1.5 我接到了一封非常懇切的推薦函:
載爵吾兄台鑒:
今日得讀友人康正果先生《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的「導言:從價值轉換到歷史還原」,甚為感動。康先生書中所收論文弟亦讀過若干,今合在一起,弟認為是「紀念中華民國百年」最上乘的作品。所以我寫此函致 兄,請細心一讀。但康先生並未托我,他是最正直最有尊嚴的學人,從不求人為他的著作之出版向任何方面說情,⋯故弟特寫此函,誠心誠意作客觀之推薦。
此函緣起如下:康先生今日在電話中偶然提到他此書不易找出版者,已得一網上出版家同意出版,其中「導言」一篇,因丘慧芬介紹與錢永祥兄,並云兄看過亦覺有興趣。弟以此請康先生暫勿與網上出版家簽約,並請他傳真「導言」與弟一讀。今讀後甚為感動與佩服,故敢逕與兄相商。倘聯經能出版,則為大好事。但弟完全尊重兄及出版社之決定,只望能予此書稿一「鄭重而嚴肅的考慮」之機,決無私毫強說人情之意味。如兄與出版社經考慮後不願出版,第絕不介意。康先生本無此想。弟慫恿他一試,故事無不諧,他也決不致見怪也。
康正果的《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就在2011年6月出版了。

就余先生個人著作的出版而言,「感受與追憶」一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正是由於聯經對於無利可圖的學術著作抱著這樣嚴肅而又慷慨的態度,我才敢歷年來將多種專題研究之作首先送請聯經考慮,《論天人之際》(2014)則是最近的一部。我早已到了老手頹唐的境地,今後是不是還有精力進行專題式的論著,那是絕對沒有把握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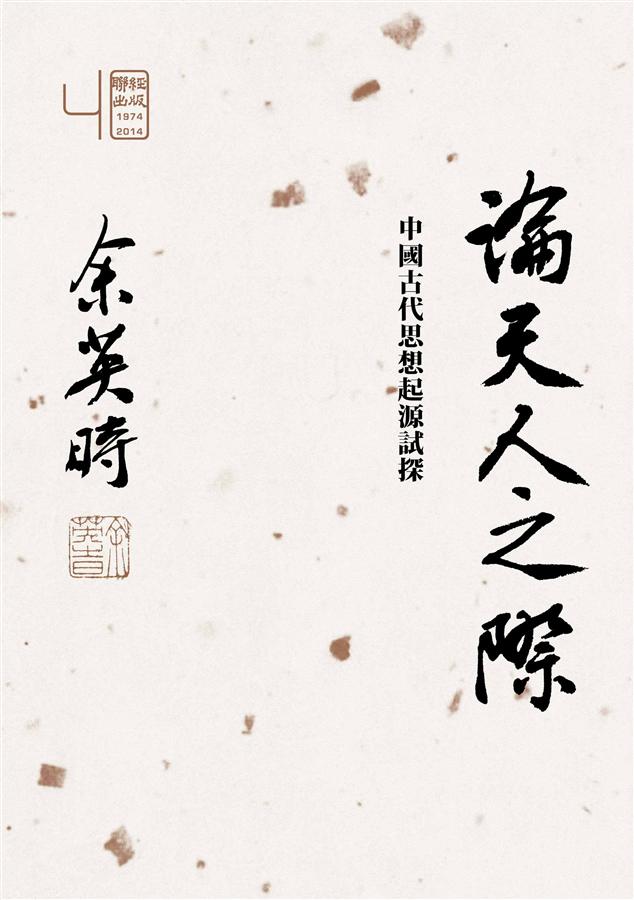
當時,我們以敬謹、感恩的心情來進行余先生以為的可能是最後一部學術專著《論天人之際》的出版工作。然而,在幾次電話聊天當中,余先生會提及他接下來最有興趣的題目是:唐代的高僧(禪宗和尚)與詩人。一方面是他的著作涵蓋春秋戰國、漢、魏晉、宋、明、清,到現代,獨缺唐代;一方面是他要經由唐代最有創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兩種人:高僧與詩人,來貫通中國的精神史。
非常遺憾的,我們再也期待不到這本鉅著的誕生了。然而,他留下了一個他所嚮往的生活世界,讓我們繼續逐夢:
「我嚮往的生活和絕大多數現代人大概沒什麼不同,即一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社會。在這種社會和文化安排下,人與人之間能互相尊重、容忍,過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絕不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但我相信社會必須以個人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個人才都能發揮他(她)的天賦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
中國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這一嚮往在今天更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為維持群體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應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覺其存在。政治力量對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這樣便會出現一種『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
一百多年來,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在追求這樣一種合理的秩序。在這一追求中,知識人的責任最大,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所以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但是這是指建設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毀一切文化傳統———包括中國的和外來的,撕毀一切則最 終必將陷入虛無主義。」(2006.12.15.,上海《東方早報》,陳怡專訪余英時:《今古逍遙知識人》)
最後,回到余先生與聯經的因緣上。今年7月16日,我向余先生提議出版一本新的論文集,及為聯經已出版的各書題字,以便重新排版,同時也向余先生介紹新任總編輯涂豐恩,敬請日後給予指教。出版新文集一事,他要我全權處理,題字則擇日進行。7月17日收到他的回信:
大函收到,共兩張:一即信,另一目錄一頁,未列各書名稱。我年邁,記憶不佳,請貴社開列一詳實書名,當一次寫成寄上。承介紹新總編輯涂豐恩先生,以後當有領教的機緣,先此致謝。
萬萬沒想到,兩個星期後,八月一日,余先生辭世。
在「感受與追憶」這篇文章中,余先生說:
最後,我必須鄭重聲明:我和聯經之間從一開始便遠遠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家的契約關係。我每次在聯經出版一本書,都覺得是一次友情的交流。
作為出版人,我們永遠記得余先生與聯經的友情,以及因為出版他的著作而對華人世界產生的深遠的影響。這段友情更將激勵我們繼續往前發展。
林載爵
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