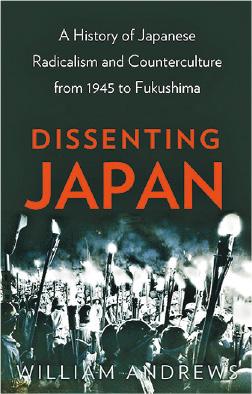

【明報專訊】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美國隨即佔領國土。
在麥克阿瑟將軍的領導下,強行建立民主體制,新日本繼而誕生。
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可謂日本的青春期。
然而這段青春並非陽光燦爛,而是充滿苦難、血淚和不甘。
William Andrews的著作Dissenting Japan詳述戰後以來日本民間的鬥爭,戳破一般人對日本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斯文、有禮、服從、井然。一九六〇年,日本國會審議修改《美日安保條約》,激起左翼、學生與民間的強烈反彈。共產黨、社會黨、總評(工會)與全學連(學生組織)共同發起鬥爭,誓要阻止立約。在他們眼中,《安保》乃美國帝國主義的產物,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是美帝的代理人,不可一世,踐踏民主。全學連發起包圍羽田機場,阻止岸信介飛往華盛頓。後來人民包圍國會,與警方激烈衝突,學生樺美智子不幸身故,成為運動象徵。最終仍無阻岸信介玩弄議事程序通過修訂。
進入一九六○年代,學生運動全面激化,大學校園(甚至高中)漫天烽火。學生的激憤和對意識形態的執念,促成分裂內鬥(內ゲバ)。全學連分裂為多個黨派:社學同、共產同、馬學同等等,馬學同再分裂為中核派、革馬派。多間大學都出現罷課鬥爭,包括日大和東大等。學生自治體組成全共鬥,目標以反抗校內不公政策開始(例如日大學生抗議校方貪污斂財),繼而發展至對抗政、商、學共同組成的資本主義產業鏈,以及自我改革。手段激烈,包括「大衆團交」禁錮教授審訊,導致有教員自殺。一九六九年東大學生佔領年安田講堂,與警察展開連日攻防戰,以鎮壓告終。
儘管學生有大約的共同目標,但派系內鬥充斥,互鬥甚至比對抗政府來得更為激烈。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機動隊犯禁攻入東大鎮壓前夕,革馬派學生撤離。中核派視此舉為在戰爭中臨陣棄甲,屬死罪。當時革馬派更關心防止全共鬥滲透自己的大本營早稻田大學,甚至展開一日的戰役,雙方各自佔據校園大樓鬥爭。中核派無法忘卻當日的背叛。一九七〇年八月,一群中核派成員在池袋綁架革馬派的海老原俊夫至據點法政大學,用鐵通毆打再刺死。事件觸發雙方互相血腥報復。
更激進的新左翼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新左翼發展出更激進的組織。其中東亞反日武裝戰線以炸彈襲擊為手段,要震懾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戰線分為三小隊,分別是狼、蝎和大地之牙。一九七四年,大道寺將司領導的狼小隊發動三菱重工爆破事件。其後繼續發動一連串企業爆破,並最終以刺殺天皇為目標。這群鬥爭者以太田龍的「窮民革命論」為指導思想,繼而發展「反日亡國論」,誓要摧毀日本帝國主義國體。另外,由共產同不斷分裂而產生的赤軍派,與革命左派結合,組成著名的聯合赤軍。赤軍派首領重信房子在一九七一年抵達黎巴嫩,參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儘管重信從未直接參與武裝行動,卻慢慢成為赤軍的象徵。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三名赤軍成員與巴解在以色列盧德機場亂槍掃射,並與警衛駁火,造成二十八人死亡。赤軍其後繼續發動一系列的劫機事件。
私刑暴力的真相
聯合赤軍最著名的慘劇,要數淺間山莊事件。赤軍成員在輕井澤的淺間山莊挾持人質,與警方對峙,以鎮壓成功落幕。然而最轟動的不是挾持本身,而是赤軍成員行私刑的細節曝光。領袖森恒夫和永田洋子要求成員不斷自我反省(「總括」),繼而互相批鬥、整肅、自殘,營造暴力的窒息氣氛,多人被殺。私刑暴力的真相令不少左翼和知識分子信仰幻滅,大眾亦徹底對新左翼失去所有同情。
新左翼和學生運動在早期依然得到部分民眾支持,然而暴力激化慢慢失去民心。社會學家安藤丈將的研究指出,日本警察調整策略,與傳媒聯手,營造警察的專業和親民形象,同時建立新左翼「過激派」的印象。國家機器武力升級,擴大機動隊、防暴和公安,展開全面鎮壓,甚至製造假案,得到輿論支持。政府也趁機提出新法制,專門對抗抗議分子。被捕者會被拘留在「待用監獄」二十三日(而且很容易延長),其間猶如人間蒸發,只能間中見律師和家人,訊問時間可以達至一日十二小時。審訊程序冗長,每月上庭一次,控方可以在無事前通知下呈上新證據。赤軍領袖塩見孝也被捕後,隨即被拘留十八個月。如此體制的用意,就是要磨滅嫌疑人的意志,使其屈服,達至百分之九十九的入罪率。
安藤認為新左翼衰敗的另一主因,是成員過分強調「自我反省」的倫理意識,放棄了改變體制的目標,轉而批判「日常性」。成員對自己的出身和特權感到歉疚,自己就是要批判的對象。正如他引述一名學生所言:「最該被否定、粉碎的就是你自己啊!」這種「自我反省」擴展至運動,對運動其他成員也有愈來愈高的道德要求。「日常性」必須永遠持續檢視,繼而造成「沒有終點的自我變革」。正如安藤所言,公與私的改革合一,令運動者毫無退路,留下失落、不安和創傷。
新公民社會力量形成
奧田英朗的推理小說《奧林匹克的贖金》以文學方式,呈現一九六○年代左翼青年的理想與失落。故事背景是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前夕。主角島崎國男是東大研究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出身秋田貧鄉。其兄在奧運工地意外身亡,成為島崎參與勞動的契機。他親身體驗了無產階級工人的工作,同時發現革命是不可能的,因為工人縱使受壓迫,也已經習慣了忍耐,沉醉於舉國上下的復興大夢。島崎決定以一人敵一國,用炸彈粉碎民族主義和復興的虛偽,要控訴世界的不公與荒謬:「不,我對政治漠不關心,只是強烈地認為,身為無產階級的一分子,必須用抵抗的方式讓統治者知道,也有不願做順從的綿羊。」島崎或許有點「中二病」,但我愈讀下去,便愈希望他能成功。因為我看到了不甘的個體,如何在龐大國家機器壓倒性的力量面前,頑抗掙扎。輝煌的國家大夢背後,往往是醜陋的現實。正如故事中一名底層工人對警察說:「只有被害人是有錢人的時候,你們才會展開偵查。即使我們遇到了麻煩,你們也不會為我們做任何事。」我想起了港珠澳大橋的犧牲者。在國家與鬥爭者之間,還有一群記者。當時部分自由派報章和周刊,初時都同情運動,並批判警察的暴力。但當暴力激化,加上警方調整策略,傳媒都漸漸歸邊。年輕記者川本三郎一直同情運動。一九七二年,他獨家訪問了一名運動者。這名運動者刺殺了一名自衛軍官,是為「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川本隨即陷入道德兩難,被記者倫理和公民道德兩邊拉扯,也受到上司、警方和檢察官的壓力,開始質疑自己的決定。結果川本決定坦白,繼而被控湮滅罪證,再被判刑。多年後他整理回憶,寫下《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為歷史留下一頁。
激憤過後,新左似乎潰敗。然而Andrews和安藤分別看到新左得以在某些場域延續,形成公民力量。Andrews指出,不公的司法制度令一群人士為被捕者和疑犯四出奔走,組成法律互助網絡。安藤則指出,「自我變革」的意識令部分日本人反省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角色,從而促成民間發起「面對面的國際合作」,例如與菲律賓的香蕉農建立平等貿易關係。另外女性運動、住民運動和志工運動慢慢興起,成為新的公民社會力量。
激烈鬥爭未能成功,剩下的可以是血淚、虛無和逃避。然而苦痛回憶也可以成為教訓,潛藏的理想可以化為新力量。沉澱過後,伺機再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