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德意志」?俾斯麥執政時期的社會
一八七八年,知名德裔作曲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試著回答這個問題,「何謂德意志人?」他從一八六五年就開始想這件事,如今十三年過去了,他還是認為自己「還不夠格更深入回答這個問題:何謂德意志?」10華格納之所以廣為人知,或許是因為他所寫的《尼伯龍根的指環》(The Ring of the Nibelung)等歌劇,但他對政治的積極態度,加上異於常人的生活方式,也都讓他成為頗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他與女演員明娜.普拉娜(Minna Planer)波折不斷的婚姻(他到處欠錢,為了躲債,他帶著普拉娜逃到倫敦與巴黎),就跟他的反猶爭議言論一樣臭名遠播。但是,他也積極參與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革命。他跟許多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一樣,對於帝國頭十年過去所取得的建樹感到幻滅。華格納打過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街頭巷戰,並且在革命後因政治因素流亡。不過,祖國終於在一八七一年統一,讓這一切似乎都值得了。但到了一八七八年,憤世嫉俗的情緒油然而生:「當年大方投票贊成『自由貿易』時,我的德意志魂興奮不已;如今,這個國度上上下下仍瀰漫著匱乏;工人餓肚子,工業一蹶不振,但『商業』倒是挺旺的。」華格納是典型的初代「德意志人」,一八七一年的他們對新社會有很高的期待,等到冀望的光榮統一跟俾斯麥帝國的現實相撞時,他們則感到不安,甚至不滿。
多數德國人起初對於自己在新德意志帝國中的未來感到樂觀。歷史學家施圖爾默(Michael Stürmer)指出,迅速的工業化帶來迅速的發展,多數人因此期待能「過著長壽、幸福的生活」,也盼望孩子的生活比自己更好。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社會各層面都能明顯感受到所謂的「進步樂觀情緒」(Fortschrittsoptimismus),美國歷史學家斯特恩(Fritz Stern)甚至說他們「全民迷醉」與「傲氣沖天」。至於個人層面,許多德國人看到進步的實質證據。薪水漲了,新就業機會浮現了,像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這樣的德國人,甚至可以在醫學領域與全歐最優秀的人媲美。不少德國國民認為德意志已經踏上一條偉大的道路,民族情感高漲。
一八七三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這股樂觀情緒。以往,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行事方式看似是德意志走向偉大與進步的筆直道路,如今卻有愈來愈多人懷疑這套體系只對社會裡的一小批商人與銀行家有利,其餘人等則遭到拋棄。這股懷疑往往以反猶論調形式出現,宣稱自由主義其實是猶太金融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分化德意志的舉動,像華格納就抱持這種想法。一八七三年確實引發保守派對自由主義的反撲,而且是社會各階層皆如是想。社會頂端的舊貴族認為自己的恐懼成真了,擁有土地與頭銜再也無法成為財富與政治影響力的保障。機械化、量產與工業的競爭已開始嚴重削弱他們的社會地位。至於社會階級的中下層,工人階級正奮力與所謂「長期蕭條」(始於一八七三年,持續到一八八○年代)的嚴重後果抵抗。相較於美國等同等級的西方國家,德國經濟受到的打擊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但投資意願低迷往往意味著糟糕的勞動條件。工人在福利、健康、安全與勞動法方面缺乏保障,只能仰賴雇主人好不好(往往不好),而雇主則無情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據經濟史家格哈特.布里(Gerhard Bry)估算,一八七一至七四年間的薪資仍保持成長,經濟成長的腳步也沒有因為一八七三年的蕭條而停步,但同一時間的生活開銷也急遽上升,增加約百分之十四,後來才降回尚可應付的水準。然而,剝削的文化已然成形,都市化與無產化已經造就出一大批憤怒的下層階級。不知不覺間,工人們的光榮祖國夢已經讓他們陷入如此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無論工作多麼努力都無所遁逃。從一八七○年代到一八八○年代,德國人移民美國的比例幾乎變成兩倍;這些移民有不少是文化鬥爭脈絡下想逃離迫害的天主教徒,但也多少是因為祖國夢的幻滅使然。
姑且不論一八七三年的財政危機,都市化的長期過程加劇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副作用,而這本身也是個挑戰。新帝國的首都柏林算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柏林的數字確實能讓人稍微對人口流動的規模有點概念。柏林先是普魯士首都,後來又成為北德意志邦聯首都,經歷一番榮景的柏林在一八七一年是德國最大的城市,居民有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等到俾斯麥在一八九○年下野時,柏林人口已成長兩倍以上,一百九十萬人以柏林為家。多數德國人仍生活在農村地區(即便到了一九一○年,大城市人口也只占全國的五分之一),但流動的趨勢已經確立。地方政府盡力管理基礎建設與住宅。但相關規定往往是都市化加劇之前制定的,無法因應如此規模的問題。柏林人口密度比都市化的魯爾地區高兩倍,情況因此比其他城市更慘。因此,「柏林租屋寨城」(Berliner Mietskaserne)的現象應運而生。最貼近德文Mietskaserne的英文是tenement(公寓)。兩者確實有一部分很類似,也就是說,承租戶居住的範圍只是建築物的一小部分,例如單層住家或一個套房,而不是整棟房子。但德語的Kaserne還有「營房」的意思,讓人聯想到單調、擁擠的斯巴達式生活環境,畫面陰鬱。房屋設計許可的規定少之又少,而不用等的便宜住宅才是當務之急,舒適度不是優先考量。一排又一排的寨城因此出現,通風、戶外空間與衛生措施都不夠。結果,許多家庭成員或同事得同住在陰暗、潮濕的生活環境。「租屋寨城」因此成為城市工人階級困境的同義詞,而柏林與漢堡的情況尤其悲慘。阿諾.霍爾茨(Arno Holz,九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等詩人對這種環境的黑暗與汙穢深感著迷:
樓頂高聳直入星空,
中庭的工廠嗡嗡作響,
租屋城寨就是這樣
還有手搖風琴的呻吟來畫龍點睛!
地下室裡鼠輩築居,
一樓擺著兌水烈酒和啤酒,
往上到六樓都是公寓
每道門後都藏著城郊的悲慘。
由於德國鐵路網設計的宗旨在於為工業服務,而不是為了強化整體人口的流動與聯繫,因此城市彼此間以及城市與港口、河流、邊境管制點之間的交通極為便利。但這種設計卻讓農村人口進退兩難。德國村鎮居民依舊仰賴步行或騎馬,地理活動範圍嚴重受限。當時沒有電話、廣播、電視或網路,想要得知當地之外的消息,唯一的途徑就是報紙。城裡還有許多人對進步感到興奮,但鄉下人這種「斷裂」的感覺一下子就變成「被拋棄」的感覺,隨之而來的不滿情緒觸發了對進步的戒心與保守反撲。鄉下人開始對現代性以及城裡那些「聰明人」深感懷疑。只有能搭到火車的人,才會對蒸汽火車頭拉著車廂出了車站,乘客舒舒服服跨越數百英里的壯闊景象感到興奮不已。其他人只懂得去恨新技術所代表的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是多麼看不起他們的生活方式。
此外,其他社會領域與地理範圍同樣有一股保守反彈。這種反彈始於一八七三年的資本體制危機,中產階級尤其深受其害。「中產階級」的範疇很廣,從老師、小企業主到大實業家都算。整體而言,他們過去積極支持自由主義運動,認為自由主義有助於德意志的統一。但在一八七三年後,資本體系經歷重整,導致一波信心危機。舊貴族對新貴族的那股嗤之以鼻,也開始滲入中產階級的腦海。軍人與貴族菁英的行事風格與生活方式開始引領潮流。一八七一年,經商的人在自己大婚之日會穿著稱頭的訂製西裝,但現在他則會試著買個軍銜,或者加入後備部隊,這樣他就可以穿軍服結婚了。無獨有偶,家具風格、髮型與風俗也開始往貴族靠攏。錢夠多、影響力夠大的人會試著買頭銜,或是與貴族成婚,如此一來就能把心心念念的「馮」(von)加到自己的名字裡。這股潮流之所以浮現,一方面是受到一八八○年代的保守轉變所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們渴望回到美好的舊時光。先前在一八七一年對上流社會的人說「你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的新貴們,如今對自己不久前得到的地位與財富感到不安,開始巴望貴族的古老世系。一旦這種趨勢與普魯士的尚武傳統,以及對「忠誠」和「力量」等所謂德意志價值的渴望相結合,那就有危險了。
這種整體保守的趨勢同樣影響社會各階層的女性。婦女時尚確實變得更輕鬆,傳統的連身裙也多被半身裙加罩衫或襯衫的實穿組合所取代。但女性整體而言仍期盼婚姻,期盼以照顧子女、家務與維護家庭溫暖的方式來支持丈夫。由於女性直到一八九一年才獲准就讀大學,因此大多數中產階級職業都是她們無法出任的。教書是唯一的例外,以往人們認為女生可以教書,但也只能教到結婚為止。工人階級女性的隊伍則出現更大的變化。前工業化時代,婦女必須務農,修補農具,幫忙收成,還要照顧家畜。早期工業化也意味著許多女性在家工作,靠做衣服的方式補貼丈夫收入。到了一八七○年代與八○年代,有愈來愈多出外工作的工人階級婦女。變化的速度不快,一八八二年時仍只有約五十萬婦女在工廠工作,因為時人仍然認為男人賺的錢若無法養家,害妻子不能在家照顧孩子,是件不光彩的事。女性多半從事低技能、單調的工廠工作,工資只有男性工人的六成,但她們的勞動條件已經在立法推動下得到若干改善。女性有產假、工時上限,法律也禁止女性上夜班或做苦工。
近年來,學界對於一八六○年代中葉開始組織起來的早期婦女運動有不少關注。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當年參與婦女運動的人,只是泰半出身資產階級、宣稱自己代表全體女性工廠工人的一小群人。早期婦女運動往往跟其他政治目標攜手合作。以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為例,她是學校老師,先生是俄羅斯革命家,實在很難代表女性工人,畢竟後者在乎的不是婦女解放,而是為了餵飽孩子,為了有棲身之所。蔡特金等早期女權主義者,體現出當時婦女工運若干元素與國際社會主義是如何交織的。至於像德意志全國婦女協會(General German Women's Association)等其他組織,其起源與願景都很中產階級,像是爭取婦女就業、上大學,以及法律上的平等。她們不願與激進的女性社會主義者合作。雙方都不代表多數德國女性,整體而言,德國婦女仍以傳統角度看待自己的角色。她們希望成為孩子們的好媽媽、先生的好太太,也因此往往跟男性一樣,對婦女組織的訴求嗤之以鼻。直到一戰前夕、期間與戰後開始有女權、選舉權與平等待遇的大規模抗議,才讓前述文化產生重大轉變。
由於帝國內部有眾多少數民族與教派,「何謂德意志」的問題依然難以回答。麥葛瑞格認為,由於德國是個沒有明確天然疆界的歐陸國家,因此很難在文化上定義「德意志」。語言的斷層線不見得跟地理或政治的界線相吻合。數百萬波蘭裔、丹麥裔與法國公民在一八七一年成為德意志帝國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對於新國家來說,他們的獨立訴求對國家的結構完整是實實在在的風險。俾斯麥對這種威脅深有體認,他一下子就指出許多帝國公敵,還說最好用「負面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的方式對付他們。也就是說,隨著時間過去,必須要強制、脅迫、激勵他們在文化與語言上成為德意志人;這一代辦不到,下一代也得辦到。為此,俾斯麥讓德語成為學校、法庭與公共生活中唯一的官方語言。由於德俄邊界兩側的波蘭文化都受到威脅,德國境內的波蘭裔學校往往為了保存文化而故意違反規定,負責推動德語化的地方政府因此經常針對波蘭學校進行檢查。政府為鼓勵德國人移居波蘭裔密集區,「稀釋」當地的語言與文化組成,因此對東普魯士土地提供貸款。此外,初中級學校、義務役與大學都刻意創造族群混合的團體與組成,以便用德意志熔爐融化外族文化。由於丹麥裔在霍爾斯泰因人數實在太少,文化與語言跟德國又很接近,當局乾脆直接忽視丹麥裔的獨立呼聲,認為假以時日整合就會自然發生。
另一方面,亞爾薩斯與洛林等併吞領土上的法裔就很難處理,當地也經常爆發抵抗事件。俾斯麥使出拿手的恩威並施,讓這些地方在帝國議會中可以有十五名代表,但在作為邦權保障的聯邦議會中卻一個代表也沒有,試圖以此穩定新占領區。更有甚者,他任命立場偏向聯邦政府的人擔任亞爾薩斯─洛林總督。此外,俾斯麥大力發展史特拉斯堡大學(Strasbourg University)以激勵留在當地的人,同時也允許想遷往法國的人離開;截至一九一四年,已有四十萬人遷居法國。持分離主義的波蘭人遭到輕蔑對待。由於帝國議會拒絕驅逐波蘭裔,受阻的普魯士政府於是在一八八五年自己動手,將三萬五千名沒有德國公民資格的波蘭裔驅逐到奧地利與俄羅斯。在這件事情上,俾斯麥扮演的角色始終引人熱議。他公開批評了這些措施,但並沒有對普魯士邦政府採取任何處罰,甚至連正式譴責都沒有。這些不客氣將國民德意志化的做法,不僅粗糙,而且沒有必要。無論是否具有「負面整合」的性質,義務役、不分族群的學校教育,以及經常把少數民族加以混合的做法,都有其同化的效果。一旦遭遇缺乏敏感度的整合措施,對德國政府抱持強烈敵意的人(尤其是法裔與波蘭裔)自然會更憤怒以對。
在德意志民族認同脈絡下,所謂的「猶太問題」也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一八七一年,德國有五十一萬二千名猶太人;甚至在統一之前,解放猶太人的討論也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俾斯麥與威廉皇帝都覺得猶太主義是宗教問題,而非族群問題,因此主張應該讓猶太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只要作為少數民族的他們能徹底融入,好好隱形,甚至可以允許他們出任公職、軍職。因此,當局鼓勵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也有一萬五千人為了仕途發展而改宗。一八七三年金融危機加深了反猶情緒,關於猶太銀行業者的老調傳言激發了人們對經濟局勢的憤怒。到了一八八○年代,新一波反猶情緒來襲,原因是東方發生了對猶太人的清洗,許多俄羅斯與波蘭猶太人因此逃往德國。這些新來的人不會說德語,教育程度不高,也缺乏專業技能。其中大部分人在普魯士落腳,尤其是柏林,而當時正值經濟危機,因此引發德國半技術工人對於薪資遭砍的擔憂。俾斯麥經常在為帝國議會中保守派與天主教盟友的言論打圓場,但他也不覺得這個問題重要到需要耗費政治資本去解決。先前談到一八八五年驅逐波蘭人,其中有四千名是猶太人;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鄉,進入反猶屠殺和其他形式的反猶暴力司空見慣的國家,俾斯麥則對此視若無睹。不過,德國的猶太人人數到一九一○年已經增加到六十一萬五千人,教育、兵役與整體文化的同化,意味著大多數猶太人跟基督徒同胞一起在俾斯麥治下的帝國相安無事。
儘管分裂、猜疑與文化不安全感確實存在,但一八七一至九○年間的德國社會確實逐漸團結起來。人格養成期的兩年義務役,對當時年紀很輕的人有轉變性的影響。不分階級、宗教與政治觀點,服役的經驗在男性心中建立了國家認同,而且是一輩子的認同,甚至延續到下一代。人們開始認為「勤奮」、「準時」、「誠實」與「精確」等是德國人與生俱來的特質,一個共享這些價值觀的社會漸漸浮現。階級、年齡、性別、宗教與民族認同的界線依然存在,但俾斯麥結束執政時,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國民大體趨向保守的,重視秩序、繁榮,以及俾斯麥所建立的聯邦。但是,民眾的愛國情緒仍然需要有不間斷的衝突來餵養,才能彌補社會肌理因為不平等、地緣孤立與文化差異所撕扯出的裂痕。
作者為德裔歷史學家。霍伊爾生於東德,父親是東德的軍官,母親是教師,她先在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學(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攻讀歷史,取得碩士學位,並於2010年左右移居英國。霍伊爾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也是倫敦國王學院的訪問學人,其歷史文章散見於《今日歷史》(History Today)和《BBC超歷史》(BBC History Extra)。霍伊爾對於今日德國與歐洲事務多有評論,亦擔任《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並固定為《旁觀者》、《每日郵報》、《不群》、《世界報》等新聞媒體供稿。《鐵與血之歌》是霍伊爾的第一本著作,2023年她另出了一本東德史新書:《圍牆之外》(Beyond the Wall: East Germany, 1949–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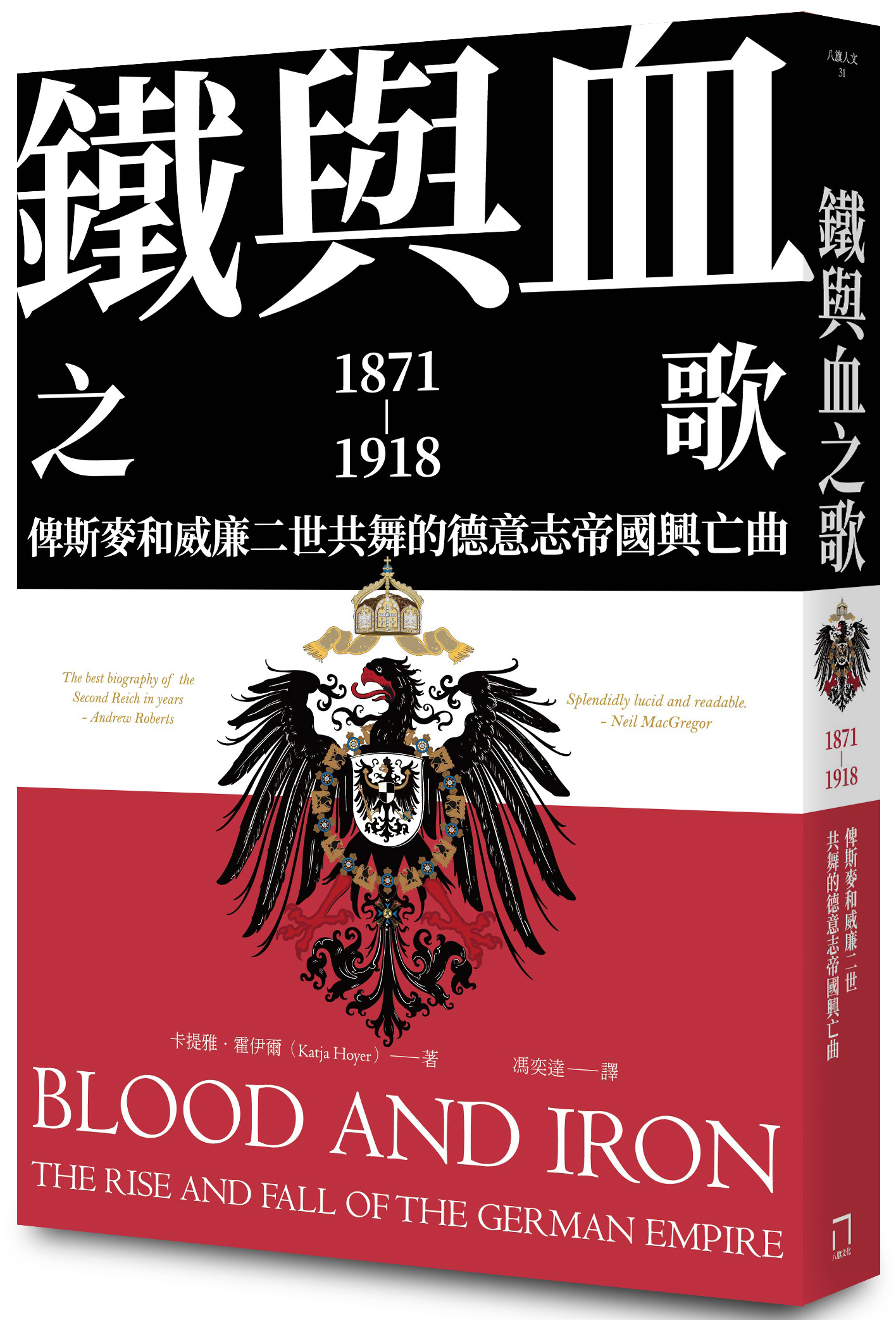
書名:《鐵與血之歌》
編者:卡提雅.霍伊爾(Katja Hoyer)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2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