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年,俄羅斯一個著名的詩人古米廖夫,因為參加白軍反抗十月革命,被作為「反革命」被處決了。(維基百科)
關於詩和政治,上世紀最年輕的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說過這麼一句話:「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這個干預當然不是說我們就是要跟它肉搏,或者說文學家都去參政。而是指我們要對政治當中的健康的因素和不健康的因素都同樣保持敏感,然後在我們詩裡邊傳達我們敏感地感受到的這些因素。
而這些因素很可能跟我們的未來有關,很可能它會像滾雪球一樣,從一個輕微的政治現實,慢慢地捲成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整個世界的命運。
布羅茨基非常喜歡、崇拜的詩人,其實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寫過一首詩,展現了我上述那種詩與政治的關係。
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十月革命發生不久。 1921年,布羅茨基的最好的朋友,也是當時俄羅斯的一個著名的詩人古米廖夫,因為參加白軍反抗十月革命,被作為「反革命」被處決了。古米廖夫也是著名詩人阿赫瑪托娃的丈夫,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曾經被稱為俄羅斯「白銀時代」最著名的詩人,而他們自稱「阿克梅派」。
最好的朋友被處死了,知道這個消息之後的曼德爾施塔姆寫了一首非常冷峻、非常令人動容的詩。這首詩就是我說的一個詩人對大時代的敏感,對政治中悸動著的種種可怕的東西的敏感,然後他嘗試呼喚他的讀者去警醒。
這首詩叫《我在屋外的黑暗中洗滌》。
我在屋外的黑暗中洗滌天空燃燒著粗糙的星星,而星光,斧刃上的鹽。寒冷溢出水桶。大門鎖著,大地陰森如其良心——我想哪裡也找不到比這清新畫布更純粹的真理。星鹽在水桶裡溶化,凍水漸漸變黑,死亡更純粹,不幸更咸,大地更移近真理和恐懼。(黃燦然譯)
詩裡的意象有著一種像寒冬裡的空氣一樣的清新,即使在中文裡邊,我們也能感到這種清晰。這種高度清晰地對悲劇的注視,讓我想起曼德爾施塔姆的後輩——俄羅斯電影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鏡頭。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被稱為詩意電影,但實際上,它也是政治的電影和歷史的電影。他拍攝他的母親在計劃經濟年代的那部電影《鏡子》;他拍攝一個藝術家在沙皇時代的掙扎,那是《安德烈·盧布廖夫》;當他拍攝一個抵抗法西斯的年輕小士兵,在大時代裡面怎樣忠於自己的命運,那是《伊凡的少年時代》。
這種種,他都是把詩意用非常清晰有力的鏡頭結構來呈現出來,就像曼德爾施塔姆這首詩裡這些意象的轉變一樣。我們可以看到,詩人非常艱難但是又非常決絕地去面對俄羅斯命運的巨變,而這個巨變折射在每一個俄羅斯人身上,尤其折射在他剛剛因為十月革命死去的朋友古米廖夫身上。
詩由一個非常戲劇化的意象開始,一個人在黑暗中走出戶外,在寒冷的俄羅斯,在戶外快要結冰的水里面去洗東西。他在洗什麼,他並沒有寫,他洗的可能是他亡友的衣服,他洗的也許是這個國家的罪惡和悲劇。
 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說過這麼一句話:「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維基百科)
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說過這麼一句話:「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維基百科)
同時在天空上,星星燃燒著——竟然是粗糙的。我們所接觸的星星,都是精緻的、優美的,像亞里士多德說的——星空是像音樂的和弦一樣互相奏鳴著的,所以在古代西方理性裡面,星空是絕對不會是粗糙的。
正如康德說,能夠永遠喚起他心中的敬畏的,只有心中的道德律和天上的星空。就是因為有了心中道德律的存在和天上不斷地看著我們的星空——就是「人在做天在看」這麼一種來自形而上的終極意義的壓力,令人能成其為人,人能夠受自己的良心所制約。
但現在這個星星燒著了,變得粗糙了,而星光落在水桶裡面,落在我正在洗的水里面,它變成了一把斧頭上的鹽,這把斧頭也許就是奪走我的朋友的性命的那把斧頭。
既然星光變成了斧頭上的鹽,那如果倒推一下這個意象,鹽所依附的斧頭呢?它就是黑夜,就跟黑夜一樣,它不分青紅皂白地降臨下來,沒有任何人能夠逃過黑夜,也沒有任何人能逃過這把斧頭,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
只是鹽留下來了,鹽是什麼?按聖經中的說法,鹽是人當中的精英,精英被殺害、或者依存在利刃上面,不得不存留在那裡,無論生還是死,慢慢這種時代的昏昧的政治狀況變成了一種寒意。
這寒意從水桶裡面冒出來,鹽融化在水里面,所以水才會慢慢變黑,就跟黑夜降臨在我們大地上,我們大地也慢慢變黑一樣。大地變黑了,詩人用了「陰森」這麼一個詞。
因為大門鎖著了,我們回不了家,我們回不到作為母親的大地的懷抱裡,大地它不再敞開接納我們,就像剛才說的星空不再呼喚道德感,兩者都不再庇護我們,於是我們的良心也昏暗了,也陰森了。
但是對於詩人來說,這正是真理浮現的時刻,死亡變得純粹,人的不幸染上了鹽,每一個人都跟精英的死亡發生了關係,這個不幸不是一個人的不幸,是整個時代的不幸。
它不斷地加劇著,但假若我們睜大眼睛去看,我們看到的除了恐懼,我們還能看到這個時代的真理。死亡漸漸跟這個我們身邊的冰凍的水融合了,像鹽一樣,漸漸地成為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將來會在未來成為我們漫長的懺悔和漫長的救贖,這個洗滌的動作就是一個渴求救贖的動作。
而且,鹽水,說不定能夠讓利刃鏽蝕。
殺戮者的洗滌和受害者的洗滌是不一樣的。殺戮者的洗滌,看過莎士比亞的戲劇《麥克白》,就會知道,麥克白夫人殺了人之後著急著去洗手,結果越洗她的手越紅,那盆水慢慢地變成了一盆血水,人只要犯了罪,那是永遠洗不掉的。
而受害者的洗滌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還原那個沒被血污染過的人,為了還原我們死去的朋友的本來面目,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僅以本文紀念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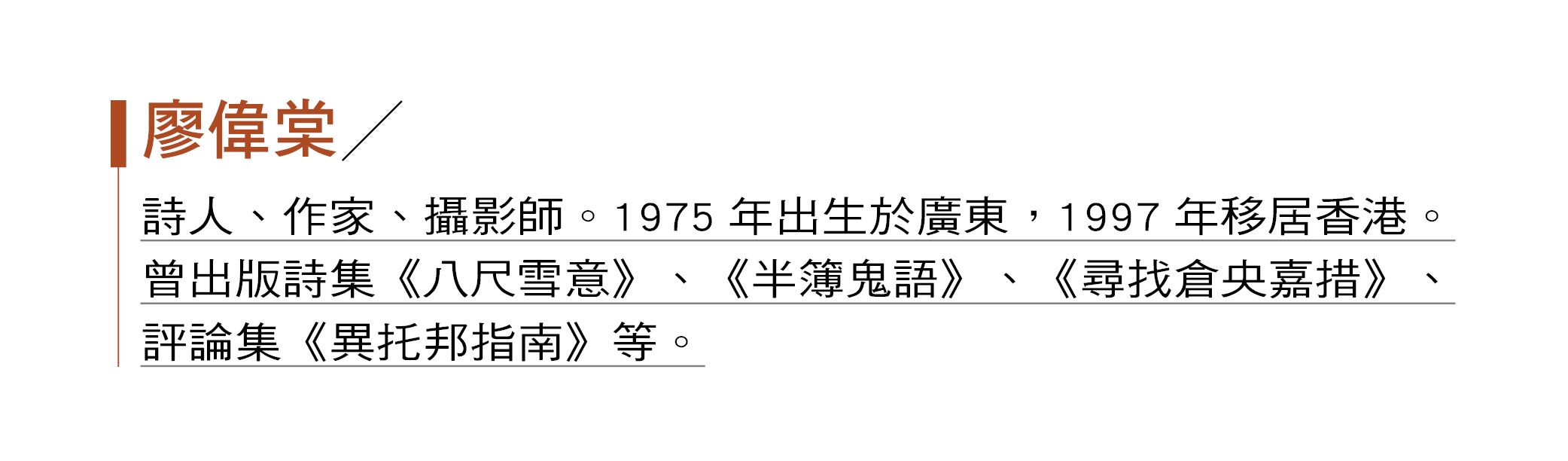
——上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